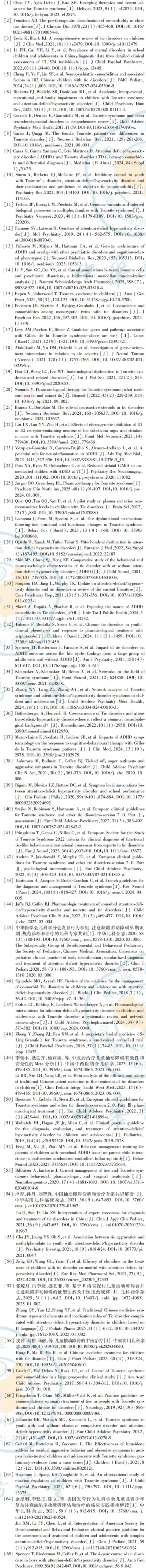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神经学组抽动障碍协作组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编辑委员会
通信作者:陈燕惠,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州350000,Email:yanhui_0655@126.com;刘智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武汉430016,Email:liuzhisheng@hust.edu.cn
DOI:10.3760/cma.j.cn101070-20250827-00660
【摘要】抽动障碍(TD)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期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两者共病率高,且对患儿社会功能及长期预后影响显著。本共识基于国内外最新研究证据,采用德尔菲法制订,旨在规范TD共患ADHD的临床诊疗。共识涵盖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特征、评估及干预策略,提出13个临床问题和20条核心推荐意见,并附推荐说明。强调多维度评估、分层治疗及多学科协作的重要。
【关键词】抽动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共患病;诊断;治疗;共识

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TD)是一种以运动抽动和/或发声抽动为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在儿童中具有较高发病率[1]。共患病(comorbidity)一词由Feinstein于1970年提出,又称共病、同病或合病,系指同一个体所患的两种或多种疾病远高于偶然发生的概率,相互之间难分主次、缺乏必然因果关系,且分别达到各自的诊断标准[2]。共患病的共同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提示它们可能存在共同的病因及病理生理机制。研究表明,85%~88%的Tourette综合征(Tourette syndrome,TS)患者至少共患1种其他神经精神疾病,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最常见的共病之一,可显著加重功能损害[3]。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神经学组抽动障碍协作组(简称中国抽动障碍协作组)组织相关专家,采用德尔菲法制订本专家共识,涵盖儿童TD共患ADHD的流行病学、共病机制、诊断及治疗策略,旨在为儿科临床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1 共识制订过程
1.1 专家组组建 由中国抽动障碍协作组和《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编辑委员会牵头,联合儿童神经内科、发育行为科、精神科、医学心理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等专家共60人参与。
1.2 文献检索 组建共识工作组,工作组成员根据国内外儿童TD共患ADHD的诊治现状,结合临床工作经验,选定13个临床问题并进行文献检索。检索中国知网、万方全文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检索式由“儿童/children”“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等中英文相关词汇及逻辑符号组合,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5年7月,语种限制为中文或英文。根据临床问题,首先通过阅读文献题目、摘要,排除不相关文献。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通读全文提取文献证据。前期文献检索发现病例报告、病例系列研究和有限数量的队列研究是现有关于TD共患ADHD诊疗建议的主要证据基础,循证医学证据低。因此,确定采用德尔菲法制订本共识。共识工作组根据文献检索结果,拟定第1轮德尔菲调查问卷,包括20条推荐意见。每个临床问题均针对TD共患ADHD进行推荐。
1.3 德尔菲调查 于2025年8月进行首轮德尔菲调查,通过问卷星及邮件形式进行,将德尔菲问卷和前期文献检索证据、综述,通过问卷星及邮件发送给共识专家组各位成员。专家组成员结合文献证据及自身经验,填写德尔菲问卷。每个问题分5级:1为强烈反对,2为反对,3为中立,4为同意,5为强烈同意。每个问题后专家均可填写补充意见。若专家填写强烈同意及同意的总比例>75%表示该条目达成共识推荐。共识工作组总结首轮德尔菲调查结果,共发出问卷60份,收回60份。
1.4 撰写与修订 共识工作组根据前期文献证据及德尔菲调查结果撰写专家共识初稿,并附推荐说明。将共识初稿发给共识专家组成员审阅,根据专家组提出的意见进行再次修改核对,确定共识终稿。
2 推荐意见及依据
临床问题1:TD共患ADHD的流行病学特征
推荐意见1:儿童TD患者中ADHD共患率为25%~70%,男性患儿风险高于女性患儿(共识度95%)。
推荐说明:儿童和青少年TD患者的患病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差异较大,最近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人群的患病率约为2.5%,且男性患者占主导地位[3-4]。值得注意的是,TD患者中ADHD的共病率高达25%~70%[5-7],表明两者共病现象极为常见。
在性别分布上,TD患者中男性显著多于女性,但女性患者的症状高峰较晚,随年龄增长缓解率更低,且成年后抽动症状导致的心理功能损害更严重[8]。女性TD患者共病ADHD的比例低于男性,且更易共患焦虑和情绪障碍[8]。从发病年龄与病程来看,TD通常在儿童期(5~10岁)起病,表现为运动抽动或发声抽动,起病时间相较于ADHD晚。ADHD同样属于儿童期发病的神经发育障碍[9],但其核心症状(如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往往比抽动症状更早出现。TD共患ADHD患者的临床表现较为复杂,执行功能受损显著[7,10],且这种共病状态可能持续至成年期,进一步影响患者远期生活质量及社会功能[8]。
临床问题2:TD共患ADHD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推荐意见2:TD与ADHD的共病机制涉及多个风险基因叠加、感染、神经炎症与免疫及环境因素交互作用,导致皮质-纹状体-丘脑-皮质(cortico-striato-thalamo-cortical,CSTC)环路内神经递质(如多巴胺、谷氨酸、γ-氨基丁酸)功能紊乱,抑制-兴奋功能失衡(共识度97%)。
推荐说明:遗传因素、感染、神经炎症与免疫及环境因素交互影响参与TD共患ADHD的发病。TD与ADHD的共病现象具有显著的遗传学基础,两者均为高度遗传影响的神经发育障碍,TD的遗传度为60%~80%[11],ADHD的遗传度高达77%~88%[12]。遗传学研究揭示两者存在部分风险基因位点重叠[13-14],可能通过共享多基因效应或通路(如突触功能调控)驱动共病。家族与双胎研究进一步支持遗传因素共享假说[15-16],TD患者的一级亲属中ADHD发病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双生子研究表明[16-17],共病主要受共同遗传因素驱动,单卵双胎的TD共病率显著高于异卵双胎。基因-环境交互作用亦不可忽视,特定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如MAOA、SLITRK1基因)在缺氧或感染及环境压力下可能加剧TD与ADHD症状[18-19]。
抑制-兴奋功能在CSTC环路中的失衡可能是产生TD及其共病的分子机制。在TD共患ADHD患者中,存在纹状体多巴胺信号传导异常、多巴胺能神经元发育异常、纹状体D2受体敏感性增高和突触前多巴胺转运体功能异常[20-22]。而ADHD患者则存在前额叶皮质和纹状体区域多巴胺信号传导不足,导致执行功能缺陷[23-24]。在TD共患ADHD患者的CSTC环路中,谷氨酸能兴奋性传递增强与γ-氨基丁酸能抑制性传递减弱并存。TD患者纹状体γ-氨基丁酸中间神经元功能减退导致对运动通路的抑制不足[21,25],而ADHD患者前额叶皮质的γ-氨基丁酸/谷氨酸比例降低与冲动控制缺陷显著相关[24]。此外,共病患者丘脑γ-氨基丁酸能神经元投射异常可能损害感觉运动信息过滤功能,导致抽动症状和注意力缺陷问题加剧[17-18]。
其他神经递质系统亦参与共病的发生。在TD共患ADHD患者中存在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水平异常,表现为脑脊液5-HT代谢物水平降低,这可能与TD患者的情绪调节障碍及强迫症状相关[26-27],并可能进一步加重ADHD的冲动行为[23]。虽然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在ADHD的注意力调控中起重要作用,但其在TD共患ADHD患者中的交互作用机制尚未明确[23,28]。
临床问题3:TD共患ADHD的临床特征
推荐意见3:一些家长或临床医师可能更多地关注抽动现象,而忽视了共患ADHD的可能。ADHD症状出现时间早于TD症状的病例,其多动/冲动行为可能掩盖或加重抽动症状,而TD症状出现时间先于ADHD症状的病例,其抽动症状也可放大ADHD相关执行功能损害。共病患儿兼有TD和ADHD的临床表现,并较单纯TD或ADHD患者有其特殊性:(1)同时具备TD和ADHD临床表现;(2)症状出现时间:ADHD核心症状(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出现时间常早于抽动症状;(3)更易合并焦虑障碍、强迫障碍及社会适应困难;(4)至青春期,共病患者其TD或ADHD症状缓解率显著低于单纯TD或ADHD患者(共识度98%)。
推荐说明:TD共患ADHD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功能障碍更为严重,这些个体表现出显著的认知缺陷、行为紊乱和心理社会功能障碍,较仅患有ADHD的患者更为突出[29-30]。研究发现,TD共患ADHD患儿表现出更高的ADHD特征,特别是多动症状(P<0.001)[31]。在9个多动症状中,有6个症状在共患组中的报告率显著高于单纯ADHD组[31]。共患组在认知控制方面表现出与ADHD组相等的缺陷,两组相比于单纯TD组和对照组均存在显著缺陷[31]。共患ADHD的TD患儿在Achenbach儿童行为问卷(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上表现出更高的外化问题评分,共患ADHD会导致TD患者的情绪和行为功能恶化[32]。研究发现ADHD共患TD的患者中30.6%出现了焦虑障碍,13.9%出现了强迫障碍[33]。由于共病间的相互影响,TD共患ADHD患者的临床表现较单纯TD患者更为复杂。父母报告表明ADHD症状出现时间常早于TD,部分原因与ADHD的核心症状(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与课堂纪律、学习行为(如上课坐立不安、学业困难)密切相关,更易被家长或教师关注有关[10]。此外,多动/冲动表现也可能掩盖抽动症状[34-35]。部分共病病例的抽动症状可能先于ADHD症状发现,也有部分患者可能因抽动现象干扰,使其ADHD行为特征被忽视[5-7]。共病患者至青春期其TD或ADHD症状的缓解率显著低于单纯TD或ADHD患者[8,36]。
临床问题4:TD共患ADHD的早期识别与诊断
推荐意见4:早期识别、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对提高TD共患ADHD患者的社会功能,改善TD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建议对存在学业困难或伴有注意缺陷、多动或冲动行为问题的6岁以上TD患儿,应尽早启动ADHD相关临床筛查和评估,并在全面临床访谈和心理行为评估基础上进行ADHD诊断与鉴别诊断。推荐“家校医(家庭-学校-医院结合)”联动监测模式,推动家长、教师、临床医师共同参与TD和ADHD行为监测,以便早期识别共病患儿,并将共病患儿推介至有开展“TD规范化门诊”的医疗机构或开展TD专病门诊的专科医师进行进一步明确诊断(共识度100%)。
推荐意见5:TD共患ADHD患者需同时满足TD与ADHD临床诊断标准,依据患儿病史、躯体和精神检查以及相关辅助检查进行共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TD和ADHD具体诊断标准建议参照《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th Revision,ICD-11)、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修订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TextRevision,DSM-5-TR)、《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is of Mental Diseases 3rd Edition,CCMD-3)中TD和ADHD的诊断标准。目前临床上以DSM-5-TR中的TD和ADHD诊断标准最为常用。当患者的行为分别达到TD和ADHD的诊断标准时,方能诊断TD共患ADHD(共识度98%)。
推荐意见6:精神行为学量表评估有助于快速评估共病患者病情、社会功能及疾病严重程度。TS综合量表可用于TD行为特征、严重度及社会功能的评估,其中以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Yale global tic severity scale,YGTSS)最为常用。ADHD精神行为学评估量表,包括ADHD诊断量表父母版、Swanson,Nolan and Pelham父母及教师评定量表(Swanson,Nolan and Pelhamrating scales-Ⅳ,SNAP-Ⅳ)、Weiss功能缺陷评定量表(Weiss functional impairment rating scales,WFIRS)、Conners量表、困难儿童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children with difficulties,QCD),有助于帮助ADHD诊断评估以及部分共患有关学习及社交功能的其他情况的识别和评估(共识度98%)。
推荐说明:目前TD与ADHD的诊断缺乏特异性诊断指标,主要采用临床描述性诊断方法。共病的存在导致临床表现复杂化,加之对共病的认识不足,临床上仅满足TD或ADHD单病诊断,未对伴随的共病进行早期识别、早期诊断的现象十分常见,常导致共病诊断被延迟[37]。研究显示,抽动的波动性及初期轻微抽动行为易被误认为“坏习惯”,单纯TD从症状出现到确诊平均延迟2~5年[5,38];单纯ADHD患儿多因上学后学校适应问题而就医,诊断延迟相对较短(1~3年)[10,39]。TD或ADHD症状(如多动、冲动行为)共存时,由于症状的相互干扰,也会导致共病的识别和诊断难度增加,诊断延迟可延长至4~6年[37]。目前临床上,TD与ADHD诊断以DSM-5-TR中的TD与ADHD诊断标准最为常用。精神行为学评估量表有助于临床医师快速明确共病症状特征、严重程度及对社会功能的影响[40]。
临床问题5:TD共患ADHD的鉴别诊断
推荐意见7:诊断TD共患ADHD,需排除功能性抽动样行为(functional tic-like behaviours,FTLBs)[41],同时需与继发于其他疾病或心因性因素导致的类抽动或ADHD样表现的疾病相鉴别,如风湿性舞蹈病、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癫痫、药物源性锥体外系反应等(共识度98%)。
推荐说明:原发性TD症状易与其他疾病混淆,临床误诊并不罕见,特别是在TD发病早期或症状轻微时[42]。应与FTLBs、继发于其他疾病或病理状态(如锥体外系相关疾病、药物不良反应)、心因性因素以及其他导致类抽动和类ADHD的现象,如肌阵挛、肌张力障碍、舞蹈样动作、手足徐动症、面肌痉挛、刻板行为、强迫性行为、静坐不能、不宁腿综合征、某些类型的癫痫发作(如肌阵挛发作、痉挛发作、局灶运动发作及眼睑肌阵挛伴失神发作等)及各种感染性基底节脑炎和免疫性疾病后自身免疫性基底节脑炎等相鉴别[43]。
临床问题6:TD共患ADHD的治疗目标与原则
推荐意见8:TD共患ADHD的治疗目标是缓解核心症状,最大限度减少功能损害,提高生活质量以及学习和社交能力。治疗前应进行多维度的医学评估,明确抽动与ADHD症状的严重程度及对社会功能的影响程度、评估是否并存其他共病,优先干预对患者社会功能影响严重的症状,并同步处理其他共病(如对立违抗障碍、焦虑障碍、强迫障碍等)(共识度100%)。
推荐意见9:总体治疗原则是首先治疗对社会功能影响最大的症状。4岁以下TD共患ADHD患儿原则上不推荐药物治疗,以心理教育和基于疾病的父母行为干预为主;4~6岁TD共患ADHD患儿原则上以非药物治疗为主,不推荐药物治疗或仅在症状造成多方面显著不良影响时才建议谨慎选择药物治疗;6岁以上TD共患ADHD患儿建议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治疗,以较低用药剂量达到最佳疗效(共识度97%)。
推荐说明:TD与ADHD共病的治疗需以多维度评估为基础。应该优先干预对患者社会功能影响最严重的症状[44]。若TD与ADHD症状对患儿的社会功能均有明显影响时,应同时治疗。4~6岁TD共患ADHD患儿建议以非药物治疗为主,6岁以上TD共患ADHD患儿建议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治疗,以较低用药剂量达到最佳疗效[45]。过去10年的研究表明,TD共患ADHD患者可以同时安全地接受相应的针对性药物治疗。荟萃分析显示,用常规剂量的中枢兴奋剂(如哌甲酯)治疗ADHD,并不会诱发或加重TD[46-47],但有研究建议TD与ADHD共病时使用低剂量的中枢兴奋剂治疗ADHD或首选兼顾治疗ADHD和抽动症状的药物,如中枢α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如可乐定或胍法辛)[48]或非兴奋性药物托莫西汀或中成药(如菖麻熄风片、芍麻止痉颗粒、九味熄风颗粒)[48-50]。
临床问题7:TD共患ADHD的非药物治疗策略
推荐意见10:TD共患ADHD的非药物治疗以心理教育和认知行为干预治疗为主。建议所有共病患儿及家庭都应接受基于疾病相关的心理教育。认知行为干预治疗,如父母行为管理培训(parent training in behavior management,PTBM)适合于各年龄段TD共患ADHD患者,学龄期以上患者可以联合抽动综合行为干预(comprehens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of tic,CBIT)(共识度98%)。
推荐说明:PTBM、CBIT分别在ADHD和TD患者治疗中取得良好疗效,并且已经有相关循证证据支持。PTBM是学龄前ADHD儿童的首选治疗方法,并被强烈推荐用于其他药物治疗的ADHD患者[51]。现有研究和临床实践表明,针对ADHD患儿的PTBM可缓解核心ADHD症状,改善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及生活质量,并降低共病发生率[52]。CBIT被认为是治疗TD循证等级最高的行为干预治疗,能有效缓解抽动症状。目前认为CBIT适用于8岁以上的TD患者,对于年幼儿童CBIT可能有效,但相应证据并不充分[53]。
临床问题8:TD共患ADHD的药物治疗策略
推荐意见11:轻度TD共患ADHD建议采用基于TD或ADHD的心理教育、PTBM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干预;中度和重度TD共患ADHD推荐在心理教育的基础上采用针对性的行为治疗方法,如CBIT或ADHD执行功能训练或采用药物治疗。用于控制抽动症状的药物,如阿立哌唑、硫必利、可乐定透皮贴片、中成药(如菖麻熄风片、芍麻止痉颗粒、九味熄风颗粒)等,治疗ADHD药物如托莫西汀、哌甲酯、可乐定、胍法辛等(共识度97%)。
推荐意见12:若TD和ADHD症状均需使用药物干预时,推荐首选兼顾TD和ADHD的单药治疗,如中枢性α2肾上腺受体激动剂(如可乐定、胍法辛),或中成药(如菖麻熄风片、芍麻止痉颗粒、九味熄风颗粒)。其次,可以选择分别针对TD或ADHD症状的药物联合治疗,即用于控制抽动症状的药物联合治疗ADHD药物治疗。如需使用中枢兴奋剂(如哌甲酯)治疗ADHD,推荐降低给药剂量(如采用1/4~1/2常规治疗剂量的哌甲酯),避免大剂量使用中枢兴奋剂治疗,以免可能诱发或加重抽动症状(共识度93%)。
推荐意见13:治疗期间应密切监测患儿临床表现、社会功能状况、药物疗效及药物相互作用、不良反应事件,进行个体化治疗方案调整(共识度100%)。
推荐说明:TD共患ADHD应依据共病的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规范化和个体化综合治疗。TD与ADHD的病情严重程度均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轻度是指症状较轻,对患儿日常生活、学习或社交活动等功能无明显影响;中度是指症状较重,对患儿日常生活、学习或社交活动等功能有一定的影响;重度是指症状严重,对患儿日常生活、学习或社交活动等功能有明显影响。轻度TD患者通常采用心理教育,中度和重度TD患者推荐在心理教育的基础上采用行为治疗,若行为治疗无效或可及性受限,则采用药物治疗[54]。中枢性α2肾上腺受体激动剂(如可乐定、胍法辛)可同时缓解抽动和ADHD症状(如多动、冲动),且不良反应较低,适合作为TD共患ADHD患者单药或联合用药。根据TD或ADHD症状对社会功能影响严重度可以针对性选择相应的治疗TD或ADHD药物单用或联合使用。临床上TD治疗的一线药物是硫必利、阿立哌唑、可乐定透皮贴片等,二线药物是氟哌啶醇、利培酮、托吡酯等[54]。阿立哌唑可改善共患ADHD的TD患者的整体临床结局,但共患ADHD可能削弱其对抽动症状的缓解作用[32]。ADHD治疗的一线药物是哌甲酯和托莫西汀,二线药物是可乐定、胍法辛等[45]。
哌甲酯作为单纯ADHD患者的首选治疗药物,可改善注意力缺陷与多动冲动行为,但对TD共患ADHD患者需监测其对抽动症状的潜在加重作用;兴奋剂起始需低剂量滴定,并密切监测抽动变化[55]。若抽动恶化,可以降低哌甲酯剂量,联用或换用中枢性α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如可乐定)[44,56]。托莫西汀尤其适用于焦虑共病或兴奋剂不耐受者[44]。研究显示可乐定、胍法辛可同时缓解抽动和ADHD症状(如多动、冲动),且不良反应较低,适合作为TD共患ADHD患者单药或联合用药[46,53]。
中药分析研究显示,治疗上以白芍、熟地黄、天麻、钩藤、石决明、全蝎、珍珠母、龙骨、远志为核心药物,具有平肝熄风、化痰宁神的功效,可治疗儿童TD、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性情急躁[57]。目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治疗TD的中成药为菖麻熄风片、芍麻止痉颗粒和九味熄风颗粒[58],在药物功效上,兼有治疗抽动和缓解多动症状的作用。
临床问题9:TD共患ADHD的停药时机及减停方法
推荐意见14:当患儿症状完全缓解1~2年,在慎重评估TD和ADHD症状缓解情况、社会功能影响程度后,可谨慎尝试减停相关治疗药物(共识度90%)。
推荐意见15:减停治疗药物时,应分别评估共病患者TD和ADHD症状,仔细判断哪些症状造成社会功能受影响及影响程度。依据TD或ADHD症状缓解和社会功能恢复情况,尝试减停相应的药物治疗。无论减停何种治疗药物,停药均应循序渐进,一种一种逐步减停,停药期通常需要1~3个月以上。如减药期间症状反复,需重新评估药物治疗与症状反复之间的关联性,决定是否恢复治疗剂量(共识度97%)。
推荐说明:TD的药物治疗分多个阶段进行,从控制症状为主的急性治疗期至防止反复的巩固治疗期、维持治疗期、减量停药期,通常为1~2年[54]。采用药物治疗后,共病症状会明显缓解,加上患儿认知行为能力的提高、自我控制和执行能力的增强以及随着神经发育趋于成熟,疾病可自然缓解或部分缓解。鉴于共病症状常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解,故应进行定期随访和综合评估,药物治疗一定的疗程后,动态观察决定是否可以进行减停药物[45,54]。尤其是抽动症状具有波动性演变的特点,有时在治疗开始时,刚好在抽动症状加重的时期,可能会被认为是“无效的”甚至“有害的”;相反,如果治疗开始时间是在抽动症状自发缓解的时期,可能会被过早地认为是“有效的”。至少3个月的治疗观察期是避免这些偏差的最佳方式[43]。因此,应在TD共患ADHD患者症状缓解和功能损害恢复1年以上,在全面评估病情后谨慎尝试停药[45]。减量过程也应该缓慢,至少1~3个月。
临床问题10:告知患者和监护人(家长)观察等待是一种可接受的方法
推荐意见16:医师应告知患者和监护人(家长),对于抽动或ADHD症状不严重,导致功能损害轻微的TD共患ADHD患者,观察等待是一种可接受的方法(共识度93%)。
推荐意见17:应从“全生命周期”及“生物-心理-社会”视角开展TD共患ADHD患者临床诊疗及管理。TD共患ADHD治疗干预的重点在于消除功能损害,而不是使TD共病ADHD患者“正常化”(共识度97%)。
推荐说明:了解疾病自然病程有助于医师及患者作出治疗决策。抽动症状始于儿童期,并表现出起伏波动的病程。抽动严重程度的高峰通常发生在10~12岁,许多患儿至青春期后症状改善[54]。一项纵向研究表明,抽动的严重程度在青春期每年逐渐下降,16岁以上青少年TD患者17.7%没有抽动,59.5%仅有轻微或轻度抽动[59]。没有证据表明越早开始治疗越有效。由于抽动及ADHD症状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因此对于功能损害受影响较少的个体来说,观察等待是一种可接受的方法。由于在疾病的自然过程中部分或完全缓解,如果患者想尝试治疗,也可以采用CBIT或ADHD执行功能训练,而部分患者在疾病的自然过程中症状会部分或完全缓解,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患儿可能就不再需要药物治疗[60]。
临床问题11:谁来决定TD共患ADHD的治疗决策?
推荐意见18:TD共患ADHD的治疗决策应该由患者、监护人(家长)和临床医师共同决策(共识度97%)。
推荐说明:对TD共患ADHD患者而言,从认识疾病到疾病的评估、诊断和治疗是一个持续的过程。TD和ADHD是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临床病程长,部分患者临床症状甚至可持续终生,故干预措施侧重于消除功能损害,而不是使TD共病ADHD患者“正常化”,因此TD共患ADHD患者的治疗必须是个体化的,并基于患者、监护人(家长)和临床医师之间的协作决策,以确保每一个TD共患ADHD患者在其一生中获得可能的最佳治疗结局[50,53]。
临床问题12:多病共存TD患者的临床诊疗及管理
推荐意见19:TD共患ADHD患者较单纯TD患者更易共患其他精神行为障碍,导致多病共存现象,影响疾病预后。对多病共存患者,应建立多学科联合诊疗团队(如神经科、发育行为科、精神科、医学心理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等),以制定针对性的个体化综合治疗计划(共识度98%)。
推荐说明:TD共患ADHD患者因前额叶功能异常也易导致抑制控制障碍[7,10],焦虑障碍[33]、强迫障碍[61]、对立违抗障碍、冲动性攻击行为、破坏性行为高发[38,62]。其情绪失调的叠加效应尤为突出,25%~70%的共病患者出现暴怒发作(rageattacks)[38,63]。研究显示,多病共存TD患者青春期症状缓解率显著低于单纯TD或ADHD患者,提示多病共存状态对患者的神经发育轨迹有长期负面影响,需要进行综合诊疗管理和提供额外更专业的评估[64]。
临床问题13:TD共病ADHD的预后
推荐意见20:大多数TD共患ADHD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症状逐渐改善,成年后的社会功能无不良影响。但部分TD共患ADHD患者可能因为症状反复、迁延、认知不完善、心理教育缺失、诊疗处理不当,会有较多的心理问题及社会压力,导致社会功能受到明显影响(共识度98%)。
推荐说明:TD共患ADHD患者其临床症状会随时间推移显示出缓解的趋势。青少年TD患者抽动症状的严重程度逐年下降(YGTSS评分每年下降约0.80分,95%CI:0.58~1.01);4年内的缓解率约65%;16岁以后,17.7%无抽动症状,59.5%为轻微或中度抽动,22.8%为中度或重度抽动;共患ADHD的症状每年减少0.42分,4年内缓解率约为20%[59,65]。TD共病ADHD的青少年在抽动严重程度方面与仅患有TD的青少年无差异,但会经历更大的心理社会压力和较差的整体功能[61]。ADHD症状的严重程度是TS共患ADHD患者生活质量的最强影响因素,可能导致更多焦虑、情绪障碍、攻击性行为、行为问题、适应困难以及心理社会压力[37]。
鉴于TD共患ADHD高发,共病的存在使得临床表现更为复杂,易造成识别、早期诊断困难及治疗延误,进而影响预后。本共识的制订旨在增强对TD共患ADHD的认识,为TD共患ADHD患者提供规范化的诊疗建议。鼓励有条件的机构开设TD专病门诊,建设儿童TD规范化门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实施规范诊疗(图1)。本共识将依据新的循证证据定期更新、修订,从“全生命周期”及“生物-心理-社会”视角为TD共患ADHD患者临床诊疗提供最新指导,以期通过患者、监护人(家长)和临床医师的共同努力,加上学校和社会的支持,确保每一个TD共患ADHD患者均可获得可能的最佳治疗结局。

本共识基于现有证据制订,临床实践中需结合患儿具体情况灵活应用,并关注最新研究进展。
执笔:陈燕惠 柯钟灵
参与本共识制订的专家(按单位和姓氏拼音排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韩颖、姜玉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符娜、秦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崔霞);沧州市人民医院(王荣);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马建南);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柴毅明、孙锦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陈燕惠、胡君、柯钟灵);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陈文雄、张雅妮);哈尔滨市儿童医院(王春雨);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庞启明);河南省人民医院(任纯明);河南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王家勤);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刘智胜、孙丹、熊小丽);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陈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梁建民、杨立彬);江西省儿童医院(陈辉、钟建民);解放军总医院(杨光);空军医科大学西京医院(杨欣伟);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陈永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郑帼);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柯晓燕);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杨光路);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卞广波);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马小云、王守磊);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张风华);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高玉兴);山西省儿童医院(韩虹、孙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贺影忠);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李玲);上海市儿童医院(张元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王昕);首都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郑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崔永华、王旭);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张利亚);天津市儿童医院(张玉琴);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戎萍);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施旭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舒畅);无锡市儿童医院(华颖);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李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孙岩);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袁宝强);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胡玉蕾、汤春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高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张俊梅)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声明:脑医汇旗下神外资讯、神介资讯、神内资讯、脑医咨询、Ai Brain 所发表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脑医汇及主办方、原作者等相关权利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