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作者:李红玲,Email:1413585368@qq.com
DOI:10.3760/cma.j.cn421666-20250119-00058
【摘要】意识障碍(DOC)常继发于严重脑损伤,会显著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加重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目前,DOC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临床上亦缺乏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手段。经颅电刺激(tES)作为一种无创脑刺激技术,在促醒康复领域内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有关作用机制、临床疗效、最佳刺激参数、长期安全性等仍需深入探讨。本文就tES的促醒机制及其在DOC中的应用进展作一综述。
意识障碍(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DOC)是指由严重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脑血管意外、缺血缺氧性脑病或其它严重脑损伤引起的,以觉醒度和/或意识内容改变为特征的病理状态,可细分为昏迷(coma)、植物状态(vegetative state,VS)或无反应觉醒综合征(unresponsive wakefulness syndrome,UWS)、最小意识状态(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MCS)以及脱离最小意识状态(emergence from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eMCS)[1]。根据病程发展,DOC又可分为损伤后的急性期、觉醒度和意识逐渐改善的亚急性期以及需要长期管理并存在潜在功能恢复可能的慢性期[2]。随着急诊和重症医学的发展,神经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显著下降,但幸存者中DOC的发生率却急剧上升[3],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的生存质量,也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据估计,我国每年新增DOC患者超过10万人[4]。
目前,针对DOC仍缺乏明确有效的治疗方案,亟需寻找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促醒干预措施。对于DOC患者,首要任务是快速识别并纠正导致意识状态改变的可逆性原因(如感染、脑损伤等),干预手段除药物干预(如金刚烷胺、哌醋甲酯、左旋多巴、溴隐亭等)之外,还包括针灸、高压氧及神经调控技术等。其中无创神经调控技术是一种具有重要价值和发展前景的干预措施,具有无创、易操作、副作用小等优势,相对于侵入性神经调控更易被患者接受[5]。经颅电刺激(transcran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tES)是一种典型的无创神经调控技术,其原理是将低强度电流(一般为0~2mA,可为脉冲或直流形式)作用于大脑皮质靶区域,以调节神经活动并改善脑功能状态[5]。本文围绕tES的促醒机制、临床应用及安全性等作一综述,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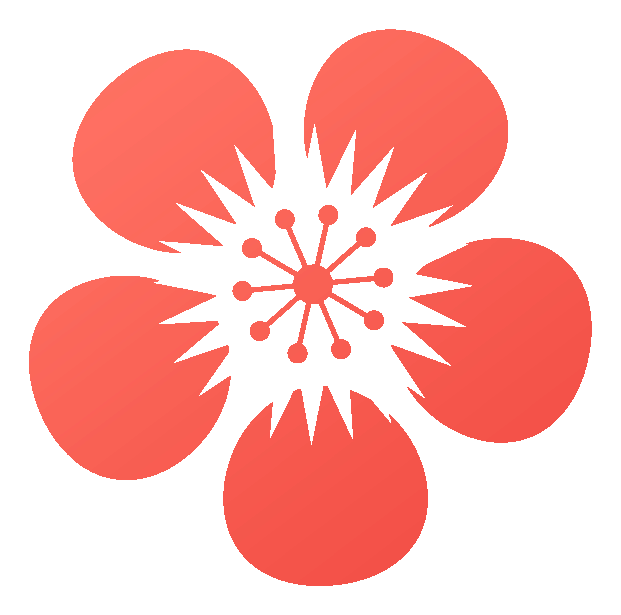
tES的分类及促醒机制
tES根据电流形式主要分为: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经颅交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alternating current stimulation,tACS)、经颅脉冲电刺激(transcranial pulse current stimulation,tPCS)及经颅随机噪声刺激(transcranial random noise stimulation,tRNS);其刺激参数及个体间差异是影响疗效的关键因素[6]。尽管tES机制研究逐渐增多,但其改善DOC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一、tDCS
作为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tES技术,tDCS可通过低强度直流电(0.5~2.0mA)调节大脑皮质兴奋性,在DOC的治疗中显示出较好的效果[5]。其机制可能如下。
1.神经元兴奋性调控:tDCS不直接引发动作电位,而是主要通过改变神经元的跨膜电位实现[7];阳极刺激促进细胞膜去极化,提高大脑皮质兴奋性;阴极刺激则导致超极化,降低大脑皮质兴奋性[8]。
2.突触可塑性调节:tDCS可促进大脑皮质神经元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 Daspartic acid,NMDA)受体表达及γ-氨基丁酸、多巴胺等神经递质释放,介导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LTP)和长时程抑制(long-term depression,LTD)[9],进而提高突触效能及神经通路的信号转导效率。
3.脑电活动与血流调节:单次前额叶tDCS可减少与意识缺失相关的慢波活动[10]。一项关于tES对脑平均血流速度影响的Meta分析表明,tES能显著增加脑动脉的血流速度和血流量[11],促进脑损伤区域的代谢与恢复。
4.脑网络功能改善:有研究者对12例受试者的主运动区和辅助运动区进行4种不同范式的tDCS,并分析其脑电信号网络特征,结果发现tDCS可以增加患者大脑功能网络的聚集程度,增强脑网络的连通性,提高脑网络的全局效率和网络信息的传递速度[12]。在一项双盲随机交叉试验中,Cavaliere等[13]回顾性评估了16例MCS患者接受单次左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tDCS后的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结果表明左侧DLPFC等脑区残留的代谢活性及其与外部控制网络的高功能连接状态,与意识恢复有关。
二、tACS
利用tACS在头皮施加低强度交流电,可在大脑中产生电场,从而调节神经活动[14]。tACS不会产生动作电位,而是引起神经元膜电位的节律性波动,并可能导致峰值时间的偏差[15]。其振幅、频率和相位是确定刺激方案时的关键考虑因素[16]。
tACS的潜在机制包括:①大脑皮质具有多个固定的频率,δ(0~4Hz)、θ(4~7Hz)、α(8~13Hz)、β(13~30Hz)、γ(30~80Hz),每个频率的夹带效应都会对大脑功能产生不同的影响[17];tACS通过在大脑中产生振荡电场,夹带局部神经活动,进而调节内源性神经振荡[18];Agnihotri等[19]运用计算机模型探究tACS诱导的皮质网络振荡变化,结果发现tACS与网络内在振荡频率一致时,可有效增强网络同步性并维持兴奋/抑制平衡;②tACS可以增强NMDA介导的突触可塑性,且可以维持较长时间[20];③两个或多个区域的tACS可以将受影响的区域同步到相同或不同的交流电相位,进而增强或减弱远程连接[21]。
与健康个体相比,DOC患者的α(8~13Hz)振荡减少,甚至消失[22-24]。理论上,tACS可以通过调节DOC患者皮质的神经振荡水平,进而改善意识状态。Zhou等[25]对28例健康对照者和33例急性或慢性DOC患者的脑电图频谱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脑电α频率的恢复可能是DOC患者认知恢复的早期敏感性特征。tACS在选择性增加健康个体的α振荡方面显示出较好的前景[26-27],其在DOC患者中的应用潜力及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三、tPCS
tPCS可将直流电转化为单相/双相脉冲电流,具有极性特异性(阳极兴奋、阴极抑制),可调节大脑皮质的兴奋性[28]。与相同刺激量的tDCS相比,长脉冲(单个脉冲持续时间长)的tPCS可更为显著地引发皮质兴奋性[29]。计算机建模结果显示,tPCS除了可以调节皮质下神经回路,并改变皮质和皮质下结构的电活动以外[30],还能改善额叶[31]和半球间神经元的连接状况[32]。提示与tDCS相比,tPCS能更显著地作用于更深层的大脑结构。
tPCS与tACS均具有频率特性,这一特性可能会影响到大脑内源性振荡活动[33]。一项随机对照交叉双盲研究,对15例健康参与者给予单次阴极tPCS干预,旨在探讨其对皮质脊髓兴奋性的影响,结果发现tPCS能够以频率依赖性方式调节大脑振荡[34]。
虽然tPCS已被证实可通过调节内源性振荡活动,来诱导神经行为和网络连接的改变,但能否将其在健康受试者中的生物学结果有效转化至DOC患者,仍需进一步研究。
四、tRNS
tRNS可将随机强度和频率的噪声电流施加于大脑皮质,因其受皮质折叠的影响较小,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不同受试者解剖学差异所导致的结果变异性,一般用于调节神经活动的tRNS振荡频谱为0.1Hz~640Hz[16]。tRNS可能通过减少抑制性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来调节兴奋/抑制比率[35]。Inukai等[36]的研究表明,在类似的刺激条件下,tRNS比tDCS和tACS能更显著地提升皮质兴奋性。
tRNS的应用较tDCS和tACS晚,目前尚不清楚tRNS是否能够通过稳态机制干扰正在进行的网络活动或大脑可塑性变化[37]。未来可以探讨特定频段tRNS对皮质兴奋性的影响[38]。此外,tRNS对DOC患者神经和行为水平上的影响及其机制,也需进一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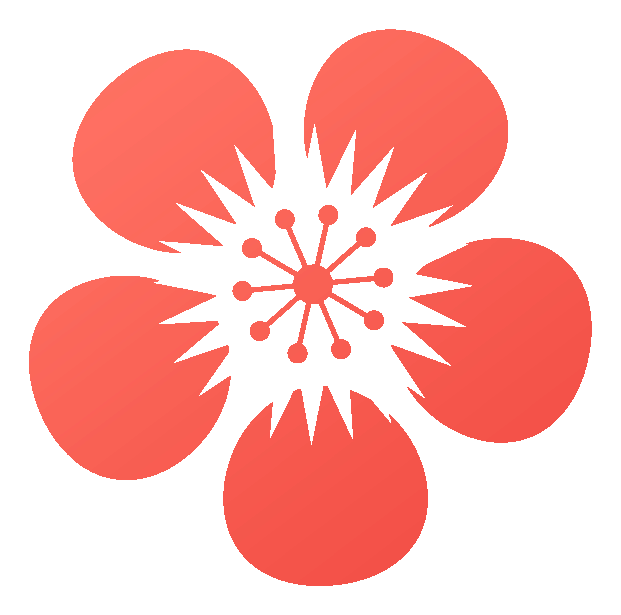
tES在促醒中的应用
一、tDCS
既往有研究报道,单次、左侧DLPFC的tDCS(2mA)可短暂改善MCS患者的昏迷恢复量表修订版(coma recovery scale-revised,CRS-R)评分[39]。近年来,相关研究重点已逐渐转向重复tDCS干预。余泽等[40]的研究发现,与常规治疗相比,辅以20次(每次20min、2mA)的tDCS能更有效地改善慢性创伤性MCS患者的意识状态,患者的CRS-R总分和听觉脑干诱发电位(brainstem auditor evoked potentials,BAEP)评分明显提高。然而,多次刺激意味着长期治疗,受患者住院时长及经济花费水平的影响,目前的研究中重复刺激次数最多的为80次[41]。
在刺激靶点方面,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发现,阳极tDCS的DLPFC刺激对改善慢性DOC患者的CRS-R评分具有显著的即时效果,而且不依赖于病程[42]。随后,研究者对不同靶点的tDCS也进行了研究,如楔前叶[43]、运动皮质[44]、后顶叶皮质[45]和额顶叶网络[41]等。但到目前为止,研究结论较为统一的是,针对大脑左前额叶皮质[46]的刺激可获得积极的效果。
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high-definition transcran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HD-tDCS)具有高空间分辨率等优势,利用这一技术可以更好地定位刺激靶点,通过靶向特定的大脑区域来调节神经活动,产生比传统tDCS更持久的可塑性变化[47]。Wang等[48]研究发现,对8例DOC患者进行连续14d的HD-tDCS皮质刺激,可以有效提高DOC患者的意识水平。Zhang等[49]对15例UWS患者和20例MCS患者给予连续14d的HD-tDCS干预,结果发现MCS患者静息态功能性脑网络中的β、γ波段的局部和全局信息处理呈增加趋势,而UWS患者在这两个波段中未表现出明显变化。
在介入时机方面,一项针对78例TBI后DOC(超过1周)患者的随机双盲临床对照试验发现,tDCS可改善患者的部分神经生理学参数,但对临床结果无明显影响[50]。池林等[51]研究发现,对病程3个月以内的DOC患者辅以tDCS治疗的效果较好。但Martens等[52]对27例慢性MCS患者(病程最短10个月、最长33年,中位数8年)进行基于家庭干预的tDCS治疗,结果显示在个体水平上,有6例(22%)患者出现了新的意识表现,考虑与神经可塑性有关,推测认为给予DOC患者较长时间的tDCS治疗,可能会收获有益效果。目前的研究从DOC急性期到慢性期均有涉及,但大部分研究病例的病程集中在1~12个月,可能与急性期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应用镇静药物、诊断困难等相关,而病程时间越长,促醒干预的效果越有限,故DOC患者的tDCS最佳介入时机,仍需进一步研究。
在刺激参数方面,王珊珊等[53]观察了不同tDCS方案(1mA、20min、每日2次;2mA、20min、每日2次;假刺激)对MCS患者的治疗作用,结果发现tDCS可改善MCS患者的意识状态,且2mA、20min、每日2次的tDCS对患者的治疗效果最明显。«慢性DOC康复中国专家共识»推荐将DLPFC、初级感觉运动皮质、前额叶作为阳极tDCS干预靶区,每次20min,电流密度40~56μA/cm2,刺激10d,可进行1~2个疗程[54]。
综上所述,tDCS在DOC促醒方面显示出明确的效果,且多针对的是MCS患者,考虑原因可能是tDCS治疗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大脑的可塑性,而MCS患者相对于VS/UWS患者来说,功能保留相对完整,大脑更具可塑性。刺激靶点以左侧DLPFC为主,初级运动皮质、楔前叶、角回次之,从单一靶点向多个靶点发展。tDCS干预基本上以阳极刺激为主,相关研究也较多。刺激强度大多选择2mA,每次20min。在刺激次数方面,重复多次干预的刺激次数尚缺乏统一的标准,虽然增加tDCS的刺激次数可能会获得更好、更持久的治疗效果,但潜在累积效应及长时间或密集刺激的安全性仍然未知。因此,有关DOC患者在不同病理、病程条件下的tDCS方案,仍需进一步研究及探讨。
二、tACS
Naro等[55]研究证实,单次、右侧的DLPFC-tACS(γ频带,10min)可以短暂地恢复慢性DOC个体的脑网络连接中断,帮助临床医生区分MCS与UWS患者;tACS可能在额叶区域内和跨额顶叶网络的范围内诱发同步振荡活动,从而加强感觉运动和额顶叶关联区域之间的局部信息处理和通信。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对脑损伤DOC患者的大脑给予10Hz的重复tACS干预,旨在验证对亚急性脑损伤所致DOC患者进行多次tACS干预的可行性,以及对意识恢复、相关脑振荡和脑网络动力学的影响,但截至目前该研究结果尚未完全发布,可持续关注[56]。
tACS可以通过结合空间和频率特异性,选择性地调节正在进行的神经同步过程,并高精度的在局部大脑区域或网络中诱发神经可塑性[57]。但在DOC中应用的研究不多,其作用靶点、刺激参数、治疗时长等相关信息,尚需进一步研究。
三、tPCS
目前,tPCS仅在少数神经系统疾病(如帕金森病)患者的治疗中有所应用[58-59]。一项针对健康人的研究显示,tPCS可以提高健康受试者的言语理解能力[60]、算术能力[61],增强运动技能和认知功能[62]。提示tPCS可能有望促进MCS患者康复。
Barra等[63]随机给予12例DOC患者乳突tPCS(6~10Hz、2mA、20min)、前额叶tDCS(2mA、20min)和假刺激,记录刺激前后患者的EEG及CRS-R评分,结果发现单次乳突tPCS对患者的行为和电生理结局有显著影响。受限于相关研究少的现实情况,tPCS在DOC临床应用中的相关参数,如电极大小、刺激靶点、脉冲的频率和强度、脉宽、脉间间隔、输出波形(单相或双相)等需进一步研究,以明确其治疗作用。
四、tRNS
高频tRNS是新近的一种经颅刺激方式,当将基于白噪声形式的振荡频谱作用于大脑皮质时,能够对皮质兴奋性产生持久的影响[64-65]。Mancuso等[65]在9例VS/UWS患者中使用靶向DLPFC的tRNS,并通过多个行为学量表和EEG的组合评估疗效,发现在改善意识或EEG数据方面,试验组和假刺激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仅有1例患者在tRNS后从VS/UWS改善为MCS。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tRNS可以改善感知,促进神经可塑性,提示其具有潜在的临床效用[66]。
目前,tRNS已被纳入促进DOC患者意识恢复的潜在干预措施[64-68]。但鉴于其有效性尚未完全得到确定,故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查tRNA在促进严重脑损伤后意识恢复方面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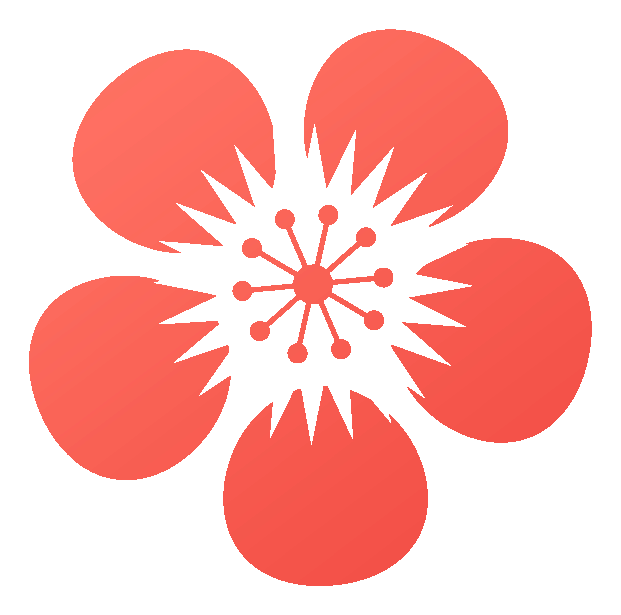
tES的安全性
tDCS的主要风险是可能诱发癫痫发作,但总体安全性良好。Sun等[50]研究发现,有10%的参与者在长时程tDCS后出现短暂的轻微皮肤发红。而在Barra等[63]的研究中,患者在接受tDCS和tPCS干预后,并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提示可行性和安全性较好。Antal等[69]详细概述了电流<4mA、每日持续时间不超过60min的低强度tES的安全性,在数千次疗程中,未报告有严重不良反应出现,常见的副作用是刺激部位的刺痛、瘙痒感或发红,通过降低电极皮肤阻抗、缓慢增加或降低tES强度、局部使用镇痛药物等,均得到了有效缓解。还有研究报道,≥95%的患者未出现任何不适,但tACS偶尔会引起幻觉或视力模糊[70]。
目前为止,有关tES电流大小、密度及其它参数的安全阈值研究较少,其参数设置的安全范围还有待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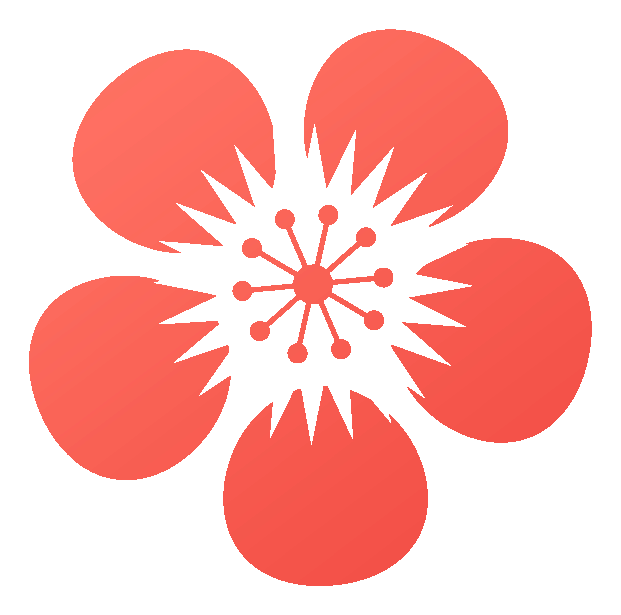
总结与展望
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tES对促醒的作用已得到了初步证实。但现有的研究存在局限性,如样本量较小、研究设计不够完善,且tES的作用机制及对意识恢复至关重要的大脑网络机制均未完全阐明;tES治疗参数不统一,刺激部位不够精确,治疗时程相对较短且缺乏长期随访评估。因此,仍需进一步优化tES参数以提高疗效,并结合每例患者的临床特征,个体化制订诊疗方案。
综上所述,与研究较多的tDCS相比,HD-tDCS技术能够聚焦大脑中的电流分布,更好地刺激特定区域;tACS可增强特定脑电频率振荡;tPCS可作用于大脑更深层区域;tRNS可增强大脑可塑性。上述方法各有优势,均能或有望成为DOC的干预手段,在明确治疗安全性的基础上,今后的研究需完善设计,针对促醒机制、疗效、刺激参数及长期影响进行大样本的研究,以期早日更好地应用于临床。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声明:脑医汇旗下神外资讯、神介资讯、神内资讯、脑医咨询、Ai Brain 所发表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脑医汇及主办方、原作者等相关权利人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