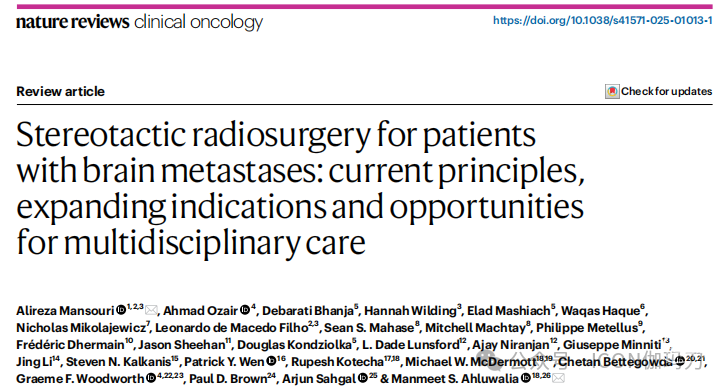
《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2025年3月19日在线发表美国Hershey Medical Center的Alireza Mansouri , Ahmad Ozair , Debarati Bhanja ,等撰写的综述《脑转移瘤患者的立体定向放射外科:目前的原则,扩大的适应证和多学科医疗的机遇。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for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current principles, expanding indic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multidisciplinary care》(doi: 10.1038/s41571-025-01013-1.)。
脑转移瘤的管理是具有挑战性的,最好通过多学科的方法进行协调。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已成为大多数寡转移性中枢神经系统受累(1 - 4个脑转移瘤)患者治疗的基石,在过去十年中,一些技术和治疗的进步扩大了SRS的适应证,包括多发转移性中枢神经系统受累(>4个脑转移瘤)、术前应用和分次SRS治疗。以及与靶向治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组合方法。例如,改进的成像和无框架头部固定技术促进了对大体积脑转移瘤或术后瘤腔或危及器官附近病变的分次SRS治疗。然而,这些机遇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包括肿瘤组织学的影响以及同步全身治疗的作用和顺序。在这篇综述中,我们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背景下的这些进展和相关挑战,以及来自全球专家组的见解,包括对当前临床实践和未来研究的建议。本文提供的更新对临床肿瘤学的所有从业者都有意义。
重点
• 影像学、患者固定技术和放射治疗计划软件的进步扩大了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治疗脑转移瘤的范围。
• 确定SRS治疗适合性的范式正逐渐从严格的脑转移瘤数目和大小的阈值转向颅内肿瘤总体积,同时越来越多地考虑到肿瘤组织学的影响。
• 分次SRS治疗可以提高疗效,同时将放射副反应的风险降至最低,特别是对于较大的脑转移瘤;然而,最佳的分次日程和剂量仍有待确定。
• 尽管正在进行使用先进成像方法的试验,但可靠地检测放射副反应,特别是区分放射性坏死和肿瘤复发,仍然具有挑战性。
•新辅助SRS治疗可减少脑膜扩散的风险,简化放射剂量计划。正在进行的试验将更好地确定患者选择策略(例如,可适应的肿瘤类型)以及手术前SRS治疗的最佳剂量,计划和时间。
•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渗透脑的靶向治疗增加了我们治疗脑转移瘤的手段。然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与SRS治疗相关的这些全身疗法的最佳序贯,或者是否可以完全忽略SRS治疗。
引言
近20%的癌症患者发生脑转移,并伴有大量神经系统疾病。全身癌症治疗的改善延长了总生存期(OS),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由于病程延长而导致脑转移瘤发生率的增加。治疗的进步也大大改善了脑转移瘤患者的局部颅内控制,尽管脑转移瘤的发展仍然预示着预后不良。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支持下,一项协作性的优先级设置工作强调了脑转移瘤患者的一些未满足的需求,以及对多管齐下的治疗方法的持续需求——目前的理想是采用多学科方法,旨在预防或延缓神经系统恶化,而继续不间断治疗颅外肿瘤。在最近开发的脑转移瘤患者跨学科医疗质量的具体指标(脑转移瘤医疗质量测量,the Brain Metastases Quality-of-Care measure, BMETS-QC)中,有三个与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有关。SRS治疗已被确立为脑转移瘤的一线治疗方式,因为随机对照试验(RCT)证明了其良好的风险-收益特征,特别是对于寡转移性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1至4个脑转移瘤),并在各种临床指南中得到推荐。然而,高质量的临床证据表明,较大的脑转移瘤、多发转移瘤中枢神经系统受累(≥5个脑转移瘤)5以及发生柔脑膜病(LMD)的高风险患者的治疗手段仍然有限。
成像和放疗传输技术的进步使得脑恶性肿瘤的分次SRS治疗成为可能,扩大了SRS治疗的适应证,特别是对于大的脑转移瘤或靠近危险的关键性中枢器官(如脑干或视神经通路)的适应证。这些方法,连同SRS与新型系统性靶向治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潜在协同作用,都很有希望,但需要进一步评估最佳剂量和分割计划、时机、治疗组合及其序贯。在过去几年中,这些和其他研究途径一直是几个主要神经肿瘤学和放射肿瘤学学会年会的主要焦点。在此,我们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随机对照试验、正在进行的研究和在现有文献的背景下讨论的与SRS治疗相关的新兴领域进行了全面的综合和评估,并提供了专家的见解,以形成一种平衡的方法,整合SRS在现代脑转移瘤管理中的不断发展的作用,特别是(1)多发转移性脑疾病的管理;(2)放射副反应(AREs)的诊断和管理进展,(3)新辅助SRS治疗的潜在作用和最佳时机,以及(4)当前关于SRS与ICIs和/或渗透脑的靶向治疗的最佳排序和组合的证据与我们理解的差距。强调这种疾病的多学科性质,本综述的目标是以一种与所有涉及脑转移瘤患者医疗的临床专业相关的方式提供证据。
目前SRS在脑转移瘤治疗中的作用
对于那些手术切除或活检被认为是不必要或不可行的患者,目前对于大多数寡转移性脑病患者来说,单独的先期SRS治疗是事实上的标准性治疗(SOC)手段。补充资料中审查了支持这一策略的证据。早期的随机对照试验(特别是放射治疗肿瘤组9508试验)首次证实了SRS治疗在寡转移性疾病患者的先期治疗中的明显应用,该试验研究了在全脑放射治疗(WBRT)中添加SRS 治疗。随后,[包括JROSG 99-1试验(n = 132)、EORTC 29952试验(n = 359)和ALLIANCE N0574试验(n = 213)的]几项随机对照试验和一项个体患者数据荟萃分析显示,在中枢神经系统寡转移性受累患者中,与单独WBRT或WBRT加SRS相比较,SRS治疗显示出有优越的神经认知和生活质量结果,以及有相似的OS。
对于手术可及的脑转移瘤,特别是较大的病变和引起神经功能障碍的病变,或者当需要活检采样来更新脑转移癌细胞的分子分析时,SOC是手术切除或活检病灶,然后进行术后SRS治疗(图1),证据见补充信息。一些随机对照试验已经证明了将SRS治疗照射切除瘤腔的治疗作用,与单独观察相比(目的是改善局部控制,如MD安德森试验所述)和与WBRT(目的是维持局部控制,同时减少认知能力下降,如ALLIANCE/CCTG N107C试验)。
总体而言,考虑到高质量的证据支持SRS治疗对除淋巴瘤、生殖细胞瘤和历史上的小细胞肺癌(SCLC)以外的大多数实体肿瘤患者的作用,不同专业协会指南对中枢神经系统寡转移患者的建议存在实质性的共识,尽管SRS治疗对后者的有希望的结果现在也有报道。其他的例外情况(尽管仍在出现),包括接受中枢系统主动全身靶向治疗的某些亚组患者,在本综述后面会做深入讨论。

图1 |挑战当前脑转移瘤的治疗范式的新兴概念。在为脑转移瘤患者选择最佳治疗方法时,必须首先考虑患者的整体表现状态和预期寿命,最好是在多学科肿瘤委员会的设置下。那些表现不佳(如Karnofsky一般表现状态量表得分<70或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状态评分3 - 4)或预期寿命有限(在许多试验中定义为≤3个月)的患者将从最佳支持治疗中获益最多。多发转移性中枢神经系统受累(>4个脑转移瘤)与寡转移性疾病(1-4个脑转移瘤)的模式不同。然而,这种基于病变数量的区分,正受到基于颅内肿瘤累积体积(CITV)考虑的挑战。对于不需要紧急手术干预的较大可触及病灶(直径约1 - 7cm)的患者,新辅助放射外科的概念正在与目前的术后放射外科方法进行评估。对于较小的脑转移瘤患者,越来越多的证据可能支持对黑色素瘤患者(特别是无症状患者)进行先期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或对某些癌基因驱动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或HER2+乳腺癌患者进行先期分子靶向中枢神经系统活性治疗,并保留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针对补救性治疗-正在进行的试验正在评估这种方法。其他组织学和/或分子亚型的证据不够有力,正在进行的调查也有限。对于局部或远处颅内肿瘤复发和/或进展,在多学科肿瘤委员会讨论的背景下,应考虑先进的成像方式(局部复发),可能的活检(确认肿瘤复发和/或排除肿瘤分子进化)。对于所有治疗方案,在可行的情况下,应不间断地持续适当的全身治疗,除非期影响到患者的整体健康。
FSRS,分次立体定向放射外科;HA-WBRT,海马回避全脑放疗。a由经治外科医生决定的可及性。b尚未确定确定较小病变的确切尺寸截断值;目前的证据支持这些方法用于直径< 1cm或体积< 2ml的病变,尽管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正在评估较大的临界值(例如,CITV < 15ml,最大脑转移瘤体积<14.2 ml或最大的脑转移瘤直径< 4cm)。c 尚未确定CITV阈值,一些正在进行的试验允许高达30毫升。d无论放射外科的时机如何,如果病变或切除瘤腔被认为很大或离危及器官太近,应考虑FSRS而不是SRS;目前正在研究的最佳FSRS计划和总剂量。
后知后觉(Considerations in hindsight)
综上所述的随机对照试验帮助构建了一个框架,并证实了SRS在治疗寡转移性脑疾病中的作用。然而,考虑到其“所有人(all-comers)”的入组方法,这些随机对照试验开创了“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方法,以相同的方式治疗所有原发性肿瘤类型的脑转移瘤。例如,大多数比较SRS与WBRT的试验将所有肿瘤类型汇总在一起,但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代表性过高;然而,他们的结论广泛适用于所有组织学。后来的随机对照试验试图提供组织学特异性和分子谱特异性的比较结果。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SRS治疗试验的另一个考虑因素是,它们是在ICIs和CNS活性分子靶向治疗的现代时代之前进行的,这些疗法大大改善了病程,不仅延长了OS,而且降低了CNS相关死亡率,增加了长期幸存者的数量。
随着分子分类、预后亚组和更有效的全身疗法的改进,根据肿瘤组织学和分子谱来治疗脑转移瘤越来越受到重视,从而形成了正在迅速融入当前实践的更个性化的管理原则和更普遍的,支持已建立的颅内疾病管理框架和指南建议的组织学不可知证据。许多SRS随机对照试验中使用的辐射剂量是另一个考虑因素,考虑到10-30%的(更常见的是有较大的病变的)患者,接受SRS治疗后仍发生颅内进展。经典的基于大小的(单次)SRS剂量阈值是在放射治疗肿瘤组90-05试验中确定的,该试验纳入有既往颅脑WBRT史的患者。在这项试验中,2000年报道了最大直径<2厘米、2 - 3厘米和3-4厘米的肿瘤的最大耐受剂量分别为24 Gy、18 Gy和15 Gy,此后根据积累的证据建议对剂量进行微小修改。鉴于SRS和相关技术的进步,以及在寡转移性疾病的一线治疗中明确建立了SRS治疗,患者往往具有更大的辐射剂量耐受性,因此人们对进一步的剂量增加非常感兴趣。如果在几个正在进行或未发表的试验(如NCT02645487和NCT02390518)中发现该方法是安全的,则该方法可能进一步改善局部控制。有趣的是,在一项试验中,35名大(直径≧ 2cm)脑转移瘤患者在切除术后接受剂量递增的新辅助SRS治疗, 2 - 3 cm肿瘤队列未达到最大耐受剂量,3-4 cm和4-6 cm队列均为18 Gy。1年局部控制率总体为76.6%,仅1例有3级ARE出现,表明有希望进行后期试验。此外,尽管已经报道了(基于下一代测序面板)用于预测放射治疗后局部控制的新的基因组评分系统,早期分子和基因组分析研究的发现已迅速成为内科管理方法的关键,但仍有待于临床转化并有意义地整合到SRS治疗决策中。
围绕SRS治疗脑转移瘤的争议
多发脑转移性疾病
尽管SRS优越的认知保护特性使其成为寡转移性脑部疾病SOC管理的关键部分,仅有条件地推荐SRS治疗有5-10个脑转移瘤的患者,通常根本不推荐给>10个脑转移瘤的患者(图1)。这种情况反映了对进一步颅内进展的速度的担忧,因此需要后续治疗,颅外疾病的控制,远处失效的风险和与放疗相关并发症,所有这些都缺乏高质量的证据。然而,广泛的努力已经放在重新评估SRS治疗在多发转移性疾病中的作用。这种重新评估部分是由JLGK0901的长期随访数据推动的,JLGK0901是日本Leksell伽玛刀协会的一项多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n = 1194),该研究为多发转移性脑疾病患者的SRS治疗相对于寡转移性脑部疾病患者的非劣效性提供了现实证据。具体而言,该研究评估了5 - 10个脑转移瘤(中位数为6个病灶;N = 208)与2 - 4个病变的患者(中位数2个病变;n = 531),发现OS无显著差异(两组中位10.8个月;HR 0.97, 95% CI 0.81-1.18;p = 0.78;(非劣效性< 0.0001)。此外,48个月时的最新分析发现,包括神经认知状态和与放疗相关并发症在内的长期并发症发生率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这表明对于10个以上脑转移瘤的患者,SRS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替代WBRT的方法。
对于>10个脑转移瘤患者,或有5-10个脑部病变但脑转移速度高的患者(通过将新脑转移瘤的数目除以初始治疗后的时间计算出的一种测量方法),在决定SRS和WBRT时,需要考虑疾病的总体发展轨迹。这些患者体内的肿瘤是否天生就更容易转移到大脑(如黑色素瘤)?总体转移性疾病负荷是否较高?对于该癌症类型(如NSCLC)和分子亚型(如HER2阳性乳腺癌),是否有良好脑外显率的全身治疗选择?患者是否同步接受治疗,身体其他部位的肿瘤是否有持续的反应?累积颅内肿瘤体积(CITV)是否比脑转移瘤的数目更重要(图1)?关于后者,一些研究表明,CITV,特别是>2ml,是比脑部病变数目更好的OS预测指标。目前,在临床实践和正在进行的试验(如III期ABC-X试验NCT03340129)中,主要基于病变数目和大小的传统阈值仍在继续实施,尽管已经出现了向CITV阈值的转变。CITV的<30 ml截断是在几十年前引入的,目前正在几个正在进行的试验中使用(如NCT02953717和III期USZ-STRIKE试验NCT05522660)。由于对脑白质病和医源性神经认知不良反应的风险而犹豫不决,也必须与患者的治疗史、病程和总体预后一起权衡。例如,患者可能已经接受了多次化疗,导致“化疗脑”(化疗患者认知能力下降)的有害影响,然后才发生脑转移。此外,患者的颅外疾病病程可能是功能衰退的原因。因此,在选择SRS和WBRT时,需要一个平衡的、个性化的方法来使临床效益最大化,同时保持大脑功能。
研究人员还努力应用新的基于成像的策略来优化选择性患者的SRS治疗计划,这些患者可以忽略或推迟WBRT。在CYBER-SPACE II期试验中,根据MPRAGE MRI序列或SPACE MRI(在检测脑转移瘤方面具有较高的诊断性能),202例1-10个脑部病变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所有转移灶(包括初始SRS治疗后出现的新病变)的SRS治疗,主要终点为无WBRT适应证(指>10个病变、LMD或耗尽SRS放射耐受性)。然而,12个月WBRT适应证率相似:SPACE组的为78.5%,MPRAGE组的为76.0% (HR 0.84, 95% CI 0.43-1.63;p = 0.59)。
考虑到SRS治疗后颅内进展的持续风险,主要是由新的远处颅内疾病复发驱动,另一种考虑的新方法是增加肿瘤电场治疗(TTFields)。一项国际III期试验(METIS,)随机分配298例因1-10个脑转移瘤而接受SRS治疗的NSCLC患者接受电场治疗(TTFields) +最佳支持治疗(BSC)或单独BSC。TTFields治疗,在SRS治疗后发生颅内进展的中位时间这一主要终点上有明显的获益(21.9个月vs 11.3个月;HR 0.67, 95% CI 0.48-0.93;p = 0.02)。由TTFields(电场治疗)引起的不良事件是轻微的(等级≤2),主要与皮肤相关。因此,这种组合策略有可能在不牺牲疗效的情况下推迟WBRT以保持生活质量。
某些临床情况可能仍然需要WBRT,例如脑转移瘤数目多的患者和/或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病变发生率高的患者,或表现不佳和/或预期寿命短的患者(由全身性疾病的程度驱动)。在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中,发现SRS治疗的初始大量脑转移瘤与远处失效的可能性较高,远处失效时发现的病变数目较多,更需要进行补救性WBRT治疗。
这种情况导致重新评估WBRT可以整合到临床工作流程中的方式。为此,涉及接受WBRT的脑转移瘤患者的III期试验表明,通过使用旨在降低神经毒性的放射传递技术(例如,海马回避型WBRT (HA-WBRT))和/或同时使用神经保护药物(如谷氨酸受体拮抗剂美金刚胺,特别是在NRG CC001试验中),认知能力下降有所减少;后一种方法为正在进行的评估谷氨酸兴奋毒性的试验提供了基本原理(NCT04785521)。一项III期试验报告,特别是对基线认知障碍较高的患者,在颅脑放疗后6个月给予(神经递质调节剂)多奈哌齐(donepezil)有一定的认知益处。
正在进行的III期NRG CC009试验(NCT04804644)正在比较SRS与HA-WBRT +美金刚胺在1-10个SCLC脑转移瘤患者中的认知结果。其他几项随机对照试验正在评估类似的方法,包括5-15个实体瘤脑转移瘤(CCTG ce7, NCT03550391), 4-15个黑色素瘤脑转移(NCT01592968), 5-20个实体瘤脑转移(NCT03075072), 4-15个实体瘤脑转移(NCT04277403)和1-10个SCLC脑转移(NCT06457906)。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涉及4-15个脑转移瘤患者的CyberChallenge试验(NCT05378633),涉及11-20个病灶患者的CAR-study B试验(NCT02953717)和针对≥5个脑转移瘤患者的WHOBI-STER试验(NCT04891471)正在比较SRS与常规WBRT,所有患者均患有各种实体肿瘤。
然而,在SRS与WBRT的头对头试验比较中,累积患者是具有挑战性的。荷兰的一项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纳入了4-10例脑转移瘤患者,由于累积缓慢而提前终止,随机化后只有29例患者(占入组目标的13%)。类似地,一项比较WBRT + SRS与单独SRS治疗5-20个脑转移瘤的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未能获得结果(该试验允许在计划MRI时确定的>30个脑转移瘤患者进行非方案治疗),因此被修改为一项平行治疗组的观察性研究(NCT03775330)。NRG-BN009 III期试验,随机分配脑转移瘤速度≥每年4个新病灶的患者(在初始SRS后第一次或第二次远处脑复发时)接受SRS或HA-WBRT治疗,也因累积不良而提前终止(NCT04588246)。这一挑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患者和临床医生之间有限的临床平衡有关。如果没有对临床细微差别的全面理解,患者更有可能倾向于“不涉及大脑”的干预措施。对于能够同时提供WBRT和SRS的临床医生来说,记忆和认知并不严格地与海马体回避的概念可能会阻止他们提供WBRT。例如,脑穹窿、杏仁核或胼胝体的白质损伤也与记忆障碍有关。目前的研究表明,HA-WBRT不能降低对穹窿的辐射剂量,对弥漫性白质脑病的风险影响有限。
总体而言,高度适形放疗(如SRS或HA-WBRT)比常规的WBRT能带来更高的认知恢复,这在对III期N107C、N0574和CC001 RCTs的个体患者数据汇总分析中得到了证明。SRS治疗多发转移性疾病,也可能对认知产生不利影响,尽管程度要小得多。临床试验(如NCT04343157、NCT02277561和NCT04073966)也在研究减少脑白质损伤的创造性策略,如使用连接组学(通过弥散性神经传导束成像)来优化SRS治疗计划(图2)。评估认知能力下降的生物标志物的试验也在进行中(例如,NCT03606421和NCT04073966)。
重新定义分次SRS治疗对大的病变的治疗
SRS治疗中另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涉及可被最佳照射的最大肿瘤体积,平衡功效最大化(即肿瘤控制)和毒性最小化(即AREs)。AREs——通常也被称为更具体的术语“放射性坏死(radiation necrosis)”或“radionecrosis”——是放射治疗的典型晚期并发症,通常在放射治疗后数月至数年出现,可以在MRI上类似肿瘤复发。据报道,在直径为约 3cm的肿瘤患者中,采用单次SRS治疗的ARE发生率较高(1年的ARE发生率为18-26%,而较小的病变的1年ARE发生率为6%)。因此,剂量递减方案通常用于单次SRS治疗,涉及随着病变体积的增加而按比例减少照射剂量(即靶体积<10 ml、10 - 15 ml和10 - 15 ml分别为16、14和12 Gy)。确保接受≥12 Gy辐射(V12Gy)的非恶性脑组织体积较小(即总剂量< 8-12 ml)已被公认可降低AREs的风险。较低的V12Gy也有不利的一面,即较低的生物效应剂量(BED)被传递到肿瘤,特别是肿瘤边缘,这可能会损害局部区域控制。与单次SRS治疗相比,分次SRS (FSRS)治疗已成为获得较高BED的替代给量策略。无框架患者定位技术为这种方法提供了便利(图2)。伽玛刀平台上基于面罩的头部固定技术的出现80意味着可以跨不同平台实施可靠的分术方案。常见的每日剂量分割方案包括3次× 9 Gy(总27 Gy)5次× 5 - 6 Gy (25-30 Gy)和5次× 7 Gy (35 Gy),后者提供的BED高于临床试验中较大脑转移瘤单次SRS治疗常使用的12-18 Gy 。回顾性研究评估了各种分次SRS计划。在一项对389例患者(共400个脑转移瘤)单独使用FSRS或手术后进行的分析中,三种常用的分割方案在局部控制率或ARE率上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先期手术(P = 0.049)和较小的病变大小(直径<2.5 cm;P = 0.01)是改善局部控制的独立预测因子。在294例接受360次FSRS治疗的患者中,与27 Gy (3 × 9 Gy;P = 0.03)或35 Gy (5 × 7 Gy;P < 0.01)的计划方案相比,30 Gy剂量-分次计划(5 × 6 Gy)的ARE发生率明显较低。一项对涉及220例患者接受FSRS治疗的334个脑转移瘤的研究发现,任何分5次给予低于30 Gy的剂量方案都与较差的局部控制相关(6个月和12个月的局部失效率分别为13%和33%,而接受≥30 Gy的患者为5%和19%;HR1.62;P = 0.03),与病变直径无关。然而,随着更现代的辐射输送平台的增加,局部控制率骄傲高,有报道称分5次的27.5 Gy(12个月的局部失效率为8.3%),但≤25 Gy的5次分割的控制率不高(12个月的局部失效率为23.5%;HR 0.59, 95% CI 0.36-0.98;P = 0.042), ARE率也相对较低。因此,根据所使用的放射治疗平台考虑最佳剂量分次方案是很重要的。
三个独立的荟萃分析评估了基于肿瘤体积和/或分次计划的局部控制率和ARE率。第一项研究评估了24项研究的数据,共涉及1887个脑转移灶,结果显示,病灶4 - 14ml(直径2 - 3cm)的1年局部控制率为76.7%,病灶> - 14ml(直径> - 3cm)的1年局部控制率为77.6%,与FSRS的92.9%和79.2%无统计学差异。1年ARE率仅在较小的4-14 ml病变中有显著差异(SRS组为23.1%,FSRS组为7.3%;P = 0.003),没有较大的病变(11.7% vs 6.5%;p = 0.29)。另一项荟萃分析(包括7项研究和1100名患者)分析了局部控制率和ARE率,而不是单个病变大小,并报告了FSRS优于SRS治疗的1年局部控制率(88%对81%;p = 0.018;I2 = 0%), AREs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15% vs 7%;p = 0.70)。第三项荟萃分析(15项研究和1049个脑转移灶直径为2 cm的患者)发现FSRS和SRS在1年局部控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81.6% vs 69.0%;P < 0.0001)和ARE率(8% vs 15.6%;p < 0.0001);然而,数据没有按肿瘤体积分层。这些大量的证据综合提供了局部控制(FSRS为79-93%,SRS为69-81%)和ARE率(6.5-8.0%,SRS为12-23%)的比较范围,尽管结果的差异需要进一步严格和前瞻性的评估。
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临床结果数据可以阐明哪种FSRS分割方案在放射生物学上等同于或优于单次SRS治疗,也没有FSRS与SRS获益的最佳肿瘤体积阈值。在临床实践中,较大的脑转移瘤(直径>2.5 cm)和伴有脑水肿和/或位于关键结构附近的脑转移瘤最常采用多阶段FSRS治疗。
如上所述,由于预后和放射敏感性的固有差异,原发性肿瘤组织学和分子谱的不平衡,以及同步使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也可能混淆脑转移瘤放疗方法比较研究的结果。
在现代系统治疗时代,除了分次治疗外,低剂量策略可能是某些组织学的一种选择。在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102例患者共688个源自各种实体肿瘤的脑转移瘤,中位边缘剂量为14 Gy(范围10-14 Gy)的治疗在1年和2年的局部失效率分别为6%和12%,ARE率分别为0.8%和2%。在这项研究中,在竞争风险分析中发现黑色素瘤脑转移与较高的局部失效风险相关,这表明需要较高的辐射剂量来治疗这种肿瘤类型。低剂量SRS治疗的适应证包括大体积病变,关键部位,既往邻近SRS或WBRT,以及多个小的或邻近肿瘤。
评估FSRS与SRS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正在切除和完整脑转移瘤患者中进行。III期临床试验联盟-071801以手术瘤床无复发生存期(NCT04114981)为主要终点,比较切除的脑转移瘤直径2-5厘米(允许≤3个未切除病灶<4厘米)患者术后FSRS(3次27 Gy或5次30 Gy)和SRS 治疗(12-20 Gy)。III期NRG-BN013试验(NCT06500455)和其他试验正在进行,以评估使用相似终点的完整大的脑转移瘤(NRG-BN013中直径1.0-3.0 cm的至少1个至8个病变)的3次FSRS治疗与单次SRS治疗的疗效。而II期SAFESTEREO试验(NCT05346367)比较的是1次SRS或3次FSRS (15-24 Gy)与5次FSRS (35 Gy)方案,复合主要终点为2年局部肿瘤失效或放射性坏死。III期SATURNUS试验(NCT05160818)将1 - 3个脑转移瘤(切除瘤腔直径≤4 cm)患者随机分配接受1次SRS 治疗(12-20 Gy)或6 - 7次FSRS(总30-35 Gy),主要终点为12个月的局部控制。然而,目前,尚不清楚FSRS与SRS治疗直径< 2cm的肿瘤的治疗效果,同样不清楚的是,大分割作为降低AREs风险的一种手段的有效性。随着这些试验的成熟,我们期待看到与SRS治疗相关的组织学特异性数据(表1),考虑到新兴的临床经验和回顾性分析的数据表明,SRS治疗剂量要求和原发性肿瘤类型的结果存在实质性差异,例如,黑色素瘤患者报告的高局部失效率。
表1 |与SRS治疗相关的主要组织学亚型脑转移瘤的关键临床挑战和相关含义。


有试验还在研究FSRS治疗大体积脑转移瘤(NCT02054689和NCT03412812)的安全性,最佳的高剂量水平可能有助于较好的局部控制。除了分次之外,一项随机对照试验(NCT04899908)也在研究使用放射增敏剂,如AGuIX(一种钆基纳米颗粒)来改善局部控制。

图2 |脑转移瘤患者SRS治疗的新方法和前沿。a、患者定位和治疗递送的无框架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极大地增加了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递送选择的灵活性(例如,可实现分次SRS治疗)和患者舒适度。b,尽管最佳的分割方案是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的重点,但分割SRS现在是脑转移瘤治疗的标准方法的一部分,图中列出了例子。c,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可行的情况下,新辅助SRS治疗具有优势,但病变大小的限制和手术前的时机是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的主题。d - f、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 (d)和新型靶向治疗目前正在通过临床试验进一步得到研究,以确定与SRS治疗相关的最佳治疗顺序(e)和/或组合(f)方案。g,先进的图像处理策略,如脑白质连通性评估(连接组学),有可能通过在可行的情况下改进对关键白质束的回避,来完善SRS治疗计划;这些策略也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中得到评估。CNS,中枢神经系统;TKI,酪氨酸激酶抑制剂;RTK,受体酪氨酸激酶。
使用的放射外科平台的影响
交付SRS治疗的商业平台包括但不限于伽马刀、射波刀和各种基于直线加速器(LINAC)的SRS平台,包括ZAP-X、Versa HD、Edge和TrueBeam等。这些平台可以是基于立体定向框架的或无框架的(例如,使用基于面罩的方法),其中一些结合了实时MRI制导(如Unity和MRIdian)或光学制导(如Triology)。由于技术方法、计划方案和不同中心和/或研究的患者队列的异质性,以及用户对特定适应证的特定平台的偏好和熟悉程度,历来难以对此类平台的性能进行直接比较。此外,剂量学比较受到以下方面的限制:能量选择、剂量率、使用等中心或非等中心技术、一个或多个等中心、共面或非共面光束或光束调制的治疗计划、用于处方剂量(等中心或特定等剂量线)和扩大剂量轮廓超出对比增强肿瘤边缘以确定靶体积的方法,以及所使用的计划算法。
基于伽玛刀的SRS治疗使用需要定期更换的钴-60辐射源,而基于LINAC的SRS的治疗交付时间不依赖于钴辐射源的剩余活性,因为它通过电子加速产生辐射,具有后勤优势(logistical advantages)。基于LINAC的SRS计划采用体积调制电弧治疗(VMAT),使用多个收敛的动态治疗电弧来实现与其他SRS递送方法类似的高辐射束一致性,同时由于缺乏涉及多个静态场的方法所需的顺序设置过程,减少了治疗时间。基于LINAC的SRS的快速治疗交付时间,由VMAT实现,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患者非自愿移动的风险,因此这种方法在治疗多发性转移时很有吸引力;然而,根据国际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学会(International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society)的规定,必须考虑直径< 1cm的靶的治疗。总体而言,跨技术的基准测试证明了不同SRS平台在治疗寡转移性或多发转移性脑转移瘤中的实用性,并且比较平台的随机试验没有证明肿瘤控制或ARE率的差异。
剂量异质性仍然是一个积极关注的领域,因为在靶体积内选择性地增加剂量(产生“热点”)可以使较高的剂量被递送到耐辐射的肿瘤内区域,目的是改善局部控制,而不会大幅增加AREs的风险。简而言之,使用伽玛刀系统,钴60产生的辐射与典型处方一起传递到50%等剂量线(等剂量线的示例见图3);因此,对50%等剂量线处方20Gy可产生40Gy的最大肿瘤内剂量。基于LINAC的SRS治疗传统上导致均匀的剂量分布;然而,选择性剂量递增和同时整合增强技术可以增加剂量的异质性(例如,整个病变可以用20Gy的辐射治疗,同时向病变的特定轮廓内部部分提供40Gy的剂量)。递送系统的内在差异已被证明可能导致不同的SRS治疗后转录组谱,有趣的是,肿瘤核心和外周区域之间的基因表达差异,尽管这些机制尚未与临床结果的变化联系起来。

图3| 脑转移瘤患者的| SRS和综合多学科医疗。本文提供一例具有代表性的IV期乳腺癌患者(雌激素受体阳性,孕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经多西他赛加卡培他滨全身治疗后出现9个脑转移瘤(即仅颅内进展)。为了优化患者的治疗效果,我们同意采用由放射肿瘤学和神经外科团队提供的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的多学科方法。a,轴位T1脑MRI扫描显示右侧小脑区两个转移灶(箭头)。b,轴位T1脑MRI对比增强后扫描的放大视图,显示SRS治疗计划和两个小脑转移灶的等剂量线分布。黄色等剂量线表示处方的辐射剂量(24Gy),绿色等剂量线(12Gy)表示SRS治疗的快速剂量下降。c,右前颅骨几何图显示该患者9个脑转移灶的位置。d,在SRS治疗后8周进行具有代表性的T1轴位脑MRI,显示完全缓解,先前可视化的增强脑转移瘤(感兴趣的区域用虚线圈突出显示)得到了解决。考虑到孤立的中枢神经系统进展和脑转移瘤对SRS治疗的有利反应,患者能够继续接受多西他赛加卡培他滨的全身治疗。e,在SRS治疗后5个月进行具有代表性的T1轴位对比增强后脑MRI扫描,显示持续的完全颅内反应,患者由乳腺医学肿瘤学团队维持相同的全身方案。
症状性ARE(放射副反应)的诊断和治疗
在SRS治疗后有影像学证据显示颅内疾病进展(伴随相应的临床恶化)的患者中,确定影像学表现是否反映了真实的肿瘤进展或AREs是指导下游临床决策所必需的,但仍然是一个主要挑战。某些肿瘤类型(如黑色素瘤和肾细胞癌),分子标记(包括BRAFV600突变和ALK重排)或全身联合治疗(如ICIs和曲妥珠单抗-药物偶联物 (T-DM1))与SRS治疗脑转移瘤后AREs风险增加相关(表1)。组织样本的病理评估仍然是区分脑转移瘤真实复发和AREs的金标准;AREs的典型表现包括内皮细胞损伤,血管透明化和血栓形成,纤维蛋白样坏死和出血。纤维蛋白样坏死区域通常包括泡沫状巨噬细胞,并被胶质组织包围。除了侵袭性脑活检取样的明显要求外,组织病理学评估并不总是确定的,坏死和活肿瘤的混合区域并不罕见。不同的基因组特征对应于治疗失败的类型,包括局部失效、LMD或AREs,已经在一项针对脑转移瘤的SRS治疗前瞻性试验的转化研究中得到了报道 -这些生物学差异仍有待于临床诊断或治疗目的的转化。然而,非侵袭性诊断模式有助于决定是否需要对复发性疾病或症状性AREs进行干预,长期以来一直是神经肿瘤学中未满足的需求。
在标准(结构性)脑MRI上区分放射性坏死与肿瘤复发仍然具有挑战性。为此目的,已经提出了包括在标准MRI方案中的几种成像序列,所有这些序列都具有有限的临床效用验证。表观弥散系数低提示富细胞病变(限制水的弥散),可提示肿瘤复发。考虑到AREs通常比肿瘤伴有较大程度的血脑屏障破坏和脑水肿,也有人提出将T1和T2序列之间的病变轮廓匹配作为肿瘤复发的指标。另外,简单的短间隔随访扫描可以实施,其原理是肿瘤通常具有较大的持续生长速率。评估评估AREs的先进成像方式的试验,包括PET-CT和PET-MRI,也在进行中(NCT04410367和NCT04410133)。
在过去的十年中,基于放射影像学的先进方法也被报道用于区分肿瘤复发和AREs,并在其他地方进行了全面的综述。MR灌注成像能够评估相对脑血容量(rCBV)、血流量和组织通透性,因此理论上可以区分具有高水平新生血管的复发肿瘤(同时具有较高的rCBV)和断流的坏死组织。大多数测试这种影像学方式评估AREs的研究都是回顾性的,队列规模较小,使用不同的rCBV阈值和与其他影像学序列的组合,总体诊断准确性一般。该适应证的MR灌注检查的总体表现受到多种挑战的限制,包括经常缺乏基线MR灌注成像,这排除了评估动态变化的匹配参考图像,肿瘤切除瘤腔内血液产物的污染,以及病变靠近大血管,空气窦腔和/或骨骼。磁共振波谱(MRS)能够评估组织的代谢成分,是另一种成像方式,已被评估用于区分复发性肿瘤和放射性坏死。对于肿瘤复发,预期胆碱:肌酐或胆碱:N -乙酰天冬氨酸比值升高,而在ARE s中,预期脂质:胆碱或乳酸:肌酸比值升高,或胆碱:肌酸比值降低。遗憾的是,除了对最小病变大小的要求外,尽管MRS在SRS患者中的试验仍在进行中,但迄今为止,MRS与MRI灌注在该适应证中的诊断准确性问题和技术挑战相同,仍受到限制(NCT03324360)。
PET是另一种成像工具,已被评估用于鉴别AREs和肿瘤进展。标准18F -氟脱氧葡萄糖-PET 依赖于癌细胞与坏死组织相比增加的代谢活性来进行诊断;然而,其敏感性和特异性普遍较低,18F -氟脱氧葡萄糖- PET的分辨率通常较差,脑代谢活动背景可能是影响因素。基于氨基酸的PET示踪剂,如11C-甲基-l-蛋氨酸(11C -蛋氨酸),I-3,4-二羟基-6- 18F -氟苯丙氨酸(F-DOPA)和O-(2- 18F -氟乙基)-l-酪氨酸(F-FET),更有选择性地被癌细胞吸收,因此可能提高诊断准确性,RANO PET组对脑转移瘤进行了全面审查。许多示踪剂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医疗机构需要现场回旋加速器来生成它们。临床试验评估使用示踪剂区分肿瘤和AREs的方法,这些示踪剂更容易获得,但通常用于CNS外肿瘤的PET成像,如18F -fluciclovine(用于前列腺癌),目前正在进行和/或未发表。这些试验包括FACILITATE (NCT06048094)、REVELATE (NCT04410133)和PURSUE (NCT04410367)。对23例患者的23个参考病灶进行评估(其中10例病理证实复发)的初步结果表明,在三个独立的盲法读者中,“标记”18F-fluciclovine摄取的阈值(即高于腮腺摄取的水平)转化为92-100%的敏感性和40-80%的特异性。18F -fluciclovine的最大病灶标准化摄取值是一个定量指标(曲线下面积为0.87),最大病灶标准化摄取值阈值为4.8,敏感性为80%,特异性为85% 。
辐射对被照射病灶周围的血管组织造成损伤,导致血管与周围其他组织之间的氧扩散障碍,引起局部缺氧。反过来,缺氧增加缺氧诱导因子-1α的表达,刺激反应性星形细胞分泌促血管生成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高水平的VEGF导致异常新生血管的形成,导致高通透性的血管结构紊乱和脆弱。这种异常的脉管系统增加液体渗漏到周围组织,从而促进脑水肿的发展,导致局部高颅内压,导致局部缺血和缺氧,形成一个前反馈循环,最终表现为AREs的临床症状。
糖皮质激素通常是有症状的SRE的一线治疗方法;然而,一些AREs患者可能对这些药物难治,或者可能无法在不复发ARE症状的情况下逐渐减少糖皮质激素。长期使用类固醇有相当大的全身副作用。此外,在接受ICI(用于颅外和/或颅内疾病)并出现症状性ARE的患者中,已知使用类固醇可降低ICI的疗效。抗VEGF抗体贝伐单抗可用于类固醇难治性ARE患者,但对出血性不良反应、需要重复静脉输注周期和治疗后4周内伤口愈合受损的担忧限制了该药物的广泛使用。Boswellia serrata(齿叶乳香)提取物是一种非处方抗炎化合物,已在一项非随机试验中进行了研究,该试验涉及50例SRS治疗脑转移瘤后1-3级放射性坏死患者。在这项试验中,完全缓解率为15%,另外40%的患者有部分缓解。只有3名患者出现毒性反应,均为1-2级。手术,伴随组织分析以确认,仍然是治疗药物治疗无效的放射性坏死的一种选择。与此同时,激光间质热疗(LITT)在治疗SRS治疗脑转移瘤后AREs方面显示出前景。LITT是一种微创入路,在术中图像引导(如MRI引导或立体定向引导)下,将探针(激光导管)通过颅骨插入脑组织,随后对探针尖端进行可控加热,导致组织消融。然而,由于热效应和原位消融组织的影响,术后可出现特征性脑水肿,并伴有相应的暂时性临床恶化。然而,LITT已被发现对症状管理和局部控制都是有用的,来自前瞻性多中心LAANTERN登记的数据显示,在90例活检证实为ARE的患者中,手术后1年脑转移瘤复发的累积发生率为19%。通过快速停用允许(用于ARE)的类固醇,(对于ARE之前正在使用ICI的患者)LITT有助于恢复已停用的ICI和/或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类固醇对正在进行的ICI治疗的疗效的影响。最后,考虑到可以在术中进行组织取样,(如果发现存在直接肿瘤消融),LITT为放射性坏死与肿瘤复发的组织病理学确认提供了机会。如果存在残留或复发肿瘤,这种活检取样也可以更新分子谱。正在进行的REMASTer RCT正在两个队列中招募SRS治疗后放射影像学改变的患者:肿瘤复发队列(a),随机分组到LITT后监测或LITT后大分割放疗;和一个ARE队列(B),随机分为LITT联合支持药物治疗或单独支持药物治疗(包括类固醇)(NCT05124912)。
新辅助SRS治疗的新作用
在过去的十年中,术前或“新辅助”SRS治疗脑转移瘤患者的势头有所增加,特别是那些不迫切需要手术治疗症状或组织病理学分析的患者。在这里,我们讨论了该策略的基本概念、实际挑战和新出现的临床证据。
减轻医源性脑实质及柔脑膜播散
尽管使用辅助SRS或FSRS(对于大的切除腔)实现了局部控制,但在切除腔内或附近的脑转移复发是常见的(局部失败率约为10-40%)156-158。在切除和辅助SRS或FSRS后,LMD的发展,通常具有结节表型159,被公认与神经死亡相关160,161。从理论上讲,这种局部复发可能继发于肿瘤周围浸润的标准模式(162)、未照射的癌细胞沿手术道的医源性播散(163)和/或手术期间癌细胞溢出到脑膜和脑脊液间隙(164),后一种理论得到了数据的支持,数据显示术后srs64后LMD发生率增加。在一项回顾性观察性研究中,包括180名接受脑转移切除的患者,114名接受新辅助SRS的患者(n = 114) 2年LMD发展率为16.6%,而66名接受辅助SRS165的患者的LMD发展率为3.2%。在一项235例患者的单中心观察性研究中,术后FSRS切除腔(共137个病灶)与LMD的风险显著高于未切除的完整脑转移瘤(共183个病灶;或2.30,95% ci 1.24-4.29;p = 0.008)。在切除腔体的FSRS患者中,1年和2年的LMD发生率分别为20%和24%,而在完整转移的FSRS患者中,这一比例分别为6%和10% 166。这些未经调整的比较需要谨慎解释,因为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指征混淆。同时,LMD的发展是几个正在进行的新佐剂与佐剂SRS试验的终点(补充表1)。
PROPS-BM队列研究(n = 404例患者)报道,新辅助治疗15 Gy SRS或分3次24 Gy FSRS, 2年局部复发率、LMD和任何级别ARE分别为13.7%、5.8%和7.4% 167。另一项涉及242名接受新辅助SRS治疗的患者的多中心研究显示,1年和2年的LMD率分别为6.1%和7.6%。在一项新辅助SRS随机II期试验中,对低剂量和高剂量围治疗期地塞米松进行了局部区域免疫分析(在任何比较结果中均未发现显著差异),为未来新辅助SRS试验中最大化颅内CD8+ T细胞反应提供了一个转化框架。
避免术后靶体积计划的难题挑战(Avoiding the challenge of postoperative target volume planning)
如其他文献所述,在放射治疗的一般背景下,基于组织的靶体积,包括肿瘤总体积、临床靶体积(CTV)和计划靶体积(PTV)。对于计划接受辅助SRS治疗的患者,目前的指南建议将手术瘤腔纳入治疗计划;然而,手术通道和柔脑膜并不总是包括作为术后SRS的 PTV的一部分,导致这些可能含有癌细胞的区域未得到治疗。其他难题挑战包括在轮廓勾画不规则边缘的肿瘤切除瘤腔,特别是勾画脑膜边缘的困难。由于切除瘤腔不完全塌陷、次全切除术、邻近组织梗死和/或术后瘢痕形成,可产生不规则边缘。
完整的、未切除的病变在SRS治疗剂量学计划中可以更准确地勾画轮廓,主要是因为计划的CTV与总肿瘤体积相同,不需要包括额外的或破坏的边缘(通常有1-2 mm的PTV外扩)。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邻近非恶性脑实质的偶然辐射,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对恶性组织的直接辐射暴露。在一项模拟术前与实施术后SRS的比较剂量学研究中,尽管PTV在配对分析中相似,但术前SRS估计可显著减少V12Gy(与术后SRS计划相比,平均体积减少31.8%,P = 0.0008)。与术后计划相比,术前剂量测定计划也更符合适形性(P < 0.001),病变边缘的剂量下降更陡峭(P = 0.0018)。这些发现可能解释了与辅助SRS治疗相比,新辅助SRS治疗的AREs发生率较低的原因。在一项评估新辅助SRS治疗1- 4个有症状性脑部病变的单组II期试验中,32名完成随访的患者6个月局部控制率为100%,1年LMD、AREs和远处失效率分别为4.8%、7.7%和40.8% 176。除了MRI模拟质量对SRS治疗的重要性之外,正如德国多社会工作组所全面讨论的那样,定位MRI的时间也是有意义的。从手术到SRS治疗的较长时间(大约4周)可能导致局部控制较差,尽管考虑到其形状、体积和精确位置可能随时间变化,在辅助SRS治疗的时机也必须考虑瘤腔动力学。建议应在术后1-2周内进行SRS治疗。
FSRS特有的另一个考虑因素是分次内瘤腔动力学的概念。作为正在进行的使用Unity MRI-LINAC系统(NCT04075305)评估放射治疗结果的国际MOMENTUM登记的一部分,对15名接受辅助分5次的FSRS的切除脑转移瘤的患者的分析发现,与基线相比,分3次的瘤腔体积治疗体积显著减少(钆剂增强T1c的中位相对减少为- 11.4%,T2/FLAIR序列的中位相对减少为- 8.4%,P分别= 0.009和0.032)。支持自适应性治疗计划。自适应性方法是新兴的“个性化放疗”范式的一个基本方面。
正在进行的试验和尚无答案的问题
一些正在进行的试验正在通过与辅助SRS治疗的随机比较来评估新辅助SRS治疗的作用,包括NCT03741673、NCT03750227、NCT05871307 (RADCAV,它有测试术中SRS的第三组)、NCT05438212 (NRG-BN012)和NCT04474925,或单组设置(NCT03368625)(图2和补充表1)。在剂量递减方案的背景下,存在一个难题,即对于次全切除已接受过术前SRS治疗的病变的患者,应如何处理术后残留疾病。目前,新辅助SRS治疗没有正式的剂量学建议,正在进行和/或未发表的试验(如NCT01252797)正在等待结果。
另一个问题与新辅助SRS方法缺乏脑转移瘤的病理证实有关,这可能影响保险授权和患者咨询。与后一种担忧相反,当代测试SRS治疗的临床试验中,没有一项在入组或纳入时需要基于活检的脑转移瘤确认,这表明仅通过影像学诊断假阳性的低风险可被接受。其他问题包括新辅助SRS的后勤挑战,特别是围绕该应用程序的整合。
将SRS与ICI相结合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于大多数转移性实体瘤,无论是单独治疗还是联合化疗,ICIs已成为SOC治疗的关键支柱,在控制黑色素瘤患者的颅内疾病和NSCLC190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
在临床前研究中与免疫疗法的潜在协同作用
放疗被认为不仅能直接诱导癌细胞损伤,还能促进局部免疫反应。电离辐射诱导DNA双链断裂,导致细胞凋亡和坏死,肿瘤相关抗原的释放,从而增加树突状细胞、CD4+和CD8+ T细胞的活化,以及MHC表达的上调,从而进一步增强抗原呈递(图4)。许多其他机制也促进淋巴细胞浸润到肿瘤微环境(图4)。

图4 |辐射的关键免疫效应和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潜在协同作用。辐射导致肿瘤相关抗原(TAAs)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从照射的癌细胞中释放出来,从而导致抗原呈递增强。最终,增强的抗原呈递可导致耗尽的肿瘤反应性T细胞(再)激活,从而导致免疫介导的癌细胞破坏。此外,PD-L1的上调经常发生在受辐照的癌细胞中,这可以在肿瘤反应性T细胞中诱导抑制PD-L1-PD-1信号传导。因此,将抗PD -(L)1抗体或其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抗CTLA4抗体)与SRS联合使用可以增强局部和远处肿瘤控制。APC,抗原呈递细胞;FASL, FAS配体;MHC,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TCR,T细胞受体。
单独放疗产生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不足以持久的颅内控制,因为大约30-50%的患者在长期放疗后会出现新的远处颅内病变。这种疾病的复发部分归因于隐匿性脑转移的持续免疫抑制环境,其特征是树突状细胞功能次佳和CD8+ T细胞的低丰度和/或功能损伤[This disease recurrence is attributed, in part, to the persistent immunosuppressive environment of occult brain metastases, characterized by suboptimal dendritic cell function and a low abundance and/or functional impairment of CD8+ T cells]。放疗在诱导DNA损伤的同时,也诱导癌细胞中DNA外切酶TREX1的上调,TREX1会分解胞质内受损的DNA,从而抑制免疫原性cGAS-STING信号传导。脑转移瘤的SRS治疗已被发现与肿瘤浸润性T细胞克隆被不支持抗肿瘤免疫的循环克隆所取代有关。因此,使用ICIs去除免疫激活的潜在刹车,提出了一种合理的组合方法。
一些临床前研究表明,当放疗联合ICIs时,局部肿瘤控制得到改善。放射诱导的新抗原释放,结合ICIs,重新激活肿瘤微环境中的肿瘤反应性CD8+ T细胞200(图4)。此外,抗PD -(L)1抗体可以激活尚未暴露于肿瘤抗原的T细胞,并使耗尽的T细胞恢复活力,而放射治疗则刺激原始T细胞分化和增殖,并潜在地募集T细胞,以响应释放的新抗原。在低免疫原性乳腺癌小鼠模型中,在细胞毒性T细胞活化和肿瘤浸润的驱动下,当与原发肿瘤联合照射时,观察到抗CTLA4抗体的全身抗肿瘤作用。此外,辅助ICIs减缓了未受照射的肿瘤细胞的生长,增加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数量。在同基因小鼠模型中,与单独分次放疗相比,分次放疗加抗PD -(L)1抗体可导致有效的CD8+ T细胞反应,增强局部控制、存活和对肿瘤再攻击的抵抗力。
在脑转移瘤模型中,放疗联合ICIs的临床前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表明与原发肿瘤观察到的相似的协同作用。在乳腺癌小鼠模型中,放疗已被证明能使“免疫冷”脑转移灶对ICIs敏感。
在黑色素瘤脑转移模型中的临床前研究也表明,放疗和ICI也可能协同上调参与癌细胞凋亡的基因表达,并增强与抗肿瘤B细胞激活相关的炎症反应。综上所述,这些发现表明,将ICIs与SRS治疗联合使用可能会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改善局部控制),不仅可以用于根除远处隐匿性病变(改善远处控制),而且还可能防止新的脑转移灶的出现(有可能改善OS)。
来自SRS联合ICIs的回顾性研究的证据
这些临床前研究结果在回顾性研究中得到了总结,这些研究涉及脑转移性肿瘤接受ICIs联合SRS的患者。这些研究报告了SRS与ICIs同时给予的各种益处(可变定义为在SRS治疗的1-4周内或在SRS治疗之前或之后长达5个生物半衰期内开始的ICI治疗),并且与ICIs和SRS之间较长的治疗间隔相比,反应速度更快。临床证据尤其支持ICIs与FSRS联合使用,这与临床前研究结果一致,即相比单次放疗,分次放疗联合ICIs可导致更大的免疫激活,这也与对辐射重复免疫激活的机制理解一致。在非小细胞肺癌和切除脑转移瘤的患者中,与单独FSRS相比,ICIs联合术后FSRS与改善远端颅内控制相关。
关于ICIs和SRS的最佳排序仍然存在争议。一些证据支持在SRS之前使用ICIs,作为启动免疫系统的一种手段,从而增强SRS治疗的抗肿瘤作用。然而,来自上述一项回顾性研究的数据表明,相比首先接受ICIs后再接受SRS治疗的患者接受SRS治疗后再接受ICIs的未接受过ICI的患者的总体肿瘤大小缩小更好(- 63% vs - 45%;p < 0.001)。特别是,这项大规模分析发现,初次接受ICIs的患者在接受SRS治疗后立即(在一个生物半衰期内)接受ICIs治疗具有最佳的缓解率,12个月的ARE率仅为3.2%。值得注意的是,类固醇对肿瘤反应和OS有负面影响。
重要的是,需要更好地了解与ICIs和FSRS同步治疗后的治疗相关影像学改变(TRICs)。在接受SRS治疗的患者中,联合使用ICIs与SRS治疗发生AREs的风险显著增加(HR 2.56, 95% CI 1.35-4.86;P = 0.004),与黑色素瘤脑转移的相关性最强(HR 4.02, 95% CI 1.17-13.82;p = 0.03)110。然而,TRICs不仅可以包括影像学定义的放射性坏死(即AREs),还可以包括与治疗相关的有益效果,这提供了抗肿瘤免疫激活和临床疗效的早期信号。一项涉及697例共4536个脑转移瘤患者的国际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SRS联合ICIs后TRICs与OS改善相关(无此类改变的患者中位29.0个月对23.1个月;多变量HR 0.66, 95% CI 0.45-0.96;P = 0.03)。
因此,对早期影像学改变的处理应该细致入微,密切观察是有必要的;在没有真正的肿瘤进展或症状性脑放射性坏死的情况下,TRICs可能预示着肿瘤内免疫反应的增强。
联合SRS和ICIs的试验
与单独的SRS治疗相比,ICIs和SRS的联合似乎赋予了更好的颅内控制,在大型回顾性研究中转化为OS的改善。然而,需要前瞻性注册研究和理想情况下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解决某些问题。例如,这些治疗的最佳时机或顺序仍不清楚。一项单组II期试验显示,接受抗PD -1抗体nivolumab(纳武单抗)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或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患者1年无中枢神经系统进展生存率为45.2%,随后在14天内接受SRS治疗,AREs风险未明显增加。
尽管一些评估放射联合ICIs安全性的早期试验确实有单独的SRS和WBRT组(如NCT01703507和NCT02696993) ,但SRS与WBRT联合ICIs后安全性和长期颅内控制的头对头随机比较仍待报道。评估不同ICI的试验,包括双ICI治疗联合SRS(包括NCT02696993、NCT05522660、NCT04889066、NCT04711824和基于ABC RCT的ABC- x试验(NCT03340129))目前正在进行中或仍待发表。正在进行的III期HYPOGRYPHE试验(NCT05703269)正在评估ICIs联合SRS +或3 - 5次FSRS,主要终点≥2级ARE。其他与潜在降低AREs风险相关的放射剂量策略,如个性化超分割立体定向消融手术和低剂量SRS,正在早期试验中与免疫疗法联合研究(图2和补充表2)。
SRS与现代靶向治疗的整合
现代靶向治疗,如脑渗透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和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作为治疗晚期或转移性癌症患者的额外工具,已经引发了极大的热情。值得注意的中枢系统活性靶向治疗包括但不限于奥希替尼( osimertinib)治疗EGFR突变NSCLC;阿来替尼(alectinib,)、布格替尼(brigatinib)和劳拉替尼( lorlatinib )治疗ALK重排NSCLC;克唑替尼(crizotinib)和恩曲替尼(enterrectinib)治疗ROS1重排NSCLC228,229;塞普替尼(selpercatinib)治疗RET改变的NSCLC;达非尼和曲美替尼(dabrafenib and trametinib)治疗BRAFV600突变型黑色素瘤;卡博替尼(cabozantinib)用于RCC(肾细胞癌);图卡替尼、曲妥珠单抗和卡他滨(tucatinib, trastuzumab and capacetabine)联合治疗HER2+乳腺癌;ADC曲妥珠单抗-药物偶联物(deruxtecan)(T-DXd)治疗HER2阳性或低HER2乳腺癌。其中一些新疗法的颅内活动报道,以及它们与SRS联合进行的研究,在补充信息中进行了综述。
临床决策
鉴于新出现的证据支持中枢神经系统主动全身治疗对颅外和颅内疾病的疗效,专业协会指南,特别是那些以内科肿瘤学为重点的指南,有条件地推荐(越来越多的)脑转移性疾病患者亚组的单独全身治疗,其中包含可靶向的驱动突变,针对颅脑的治疗(WBRT)。SRS或手术)可能被省略或推迟。“中枢神经系统降期治疗(CNS downstaging)”的范式也正在讨论中,即稳定但广泛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否则需要WBRT)的患者单独接受全身治疗,导致其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负担减轻,从而将一些患者转化为单独SRS治疗的候选患者。然而,考虑到高活性全身疗法的毒性和大脑中耐药亚群增殖的可能性——考虑到血脑屏障可以为耐药亚克隆创造一个避难所——所有这些都需要谨慎和数据驱动的方法。
在一线背景下,除了那些源于黑色素瘤、HER2+ /低乳腺癌和EGFR突变、ALK重排或RET改变的非小细胞肺癌的稳定、无症状的小脑转移患者外,证据可能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支持对所有癌基因驱动的实体瘤患者的局部治疗不进行局部治疗(图1和补充信息)。然而,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实践异质性。值得注意的是,中枢神经系统主动全身治疗的试验越来越多地允许较大但稳定的脑转移瘤患者入组,例如,COMBI-MB试验允许病变直径达4cm。从概念上讲,如果联合使用全身药物和SRS,全身治疗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微转移沉积和小的转移瘤,而SRS作用于明显的、可靶向的病变。尽管BRATR RCT比较靶向治疗联合SRS(最多三个病灶)与单独靶向治疗对EGFR突变、ALK重排或ROS1改变的NSCLC (NCT04193007)脑转移瘤患者的数据尚未发表,但新出现的回顾性报告表明,联合这些治疗有益。在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的Turbol -NSCLC研究中,评估了新型TKIs(奥希替尼或劳拉替尼)在TKI初始型EGFR突变或ALK重排的脑转移性NSCLC患者中,无论是接受先期SRS治疗 (n = 117)还是没有接受SRS 治疗(n = 200)的有效性,组合方法显著改善了局部中枢神经系统控制(HR 0.30, 95% CI 0.16-0.55;P < 0.001)和CNS进展时间(HR 0.63, 95% CI 0.42-0.96;P = 0.033),尽管OS相似(TKI + SRS的中位40个月,而TKI单独治疗的中位41个月;p = 0.50)。SRS治疗的益处在直径>1cm的脑转移灶患者中尤为明显。来自日本的另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证实了先期SRS联合奥希替尼的优势,与单独使用奥希替尼相比,CNS无进展生存期(HR 0.36, 95% CI 0.15-0.87)和OS (HR 0.37, 95% CI 0.16-0.87)显著提高。
一些将SRS与CNS活性疗法结合的随机对照试验正在进行中或未发表,包括OUTRUN (SRS +奥希替尼与单独奥希替尼治疗EGFR突变型NSCLC, NCT03497767), DURABLE (SRS +阿来替尼与单独阿来替尼治疗ALK重排NSCLC, NCT05987644), USZ-STRIKE/ (SRS系统治疗与黑色素瘤或NSCLC系统治疗,NCT05522660)和BEPOME-MB(SRS + 康奈非尼(encorafenib),北美替尼(binimetinib)和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与单独三药联合治疗BRAFv600突变黑色素瘤(NCT04074096)。印度的另一项III期RCT正在招募EGFR突变或ALK重排的NSCLC患者,在中枢神经系统主动治疗(NCT05236946)的背景下,比较先期和延迟颅脑放疗。
鉴于这些现代全身疗法的高活性,在与SRS联合使用时需要谨慎。例如,CNS -活性ADC T-DM1 联合SRS治疗现已被广泛认为与神经毒性增加和症状性AREs相关,可能是由水通道蛋白-4的上调驱动的。另一项研究表明,SRS联合任何ADC (恩美曲珠单抗[T-DM1]、德曲妥珠单抗[T-DXd]或戈沙妥珠单抗[sacituzumab govitecan])治疗各种实体肿瘤类型(乳腺癌占70%)的脑转移,并发ADC治疗出现症状性AREs的风险较高(调整后风险比4.31,95% CI 1.95-9.50;P < 0.001),控制既往放疗和病变体积。同时,一些评估T-DXd联合SRS治疗的研究报道了较低的症状性AREs发生率。同样,据报道,接受SRS + BRAF抑制剂治疗的黑色素瘤脑转移患者有较高的症状性AREs发生率(1年时28.2% vs .单独SRS组11.1%;P < 0.001)254,尽管其他一些研究的数据不支持这种关联。机制研究表明BRAF抑制剂是放射增敏剂,维莫菲尼(vemurafenib)比达拉菲尼(dabrafenib)更有效。与此同时,一项回顾性研究数据显示,中枢神经系统主动全身治疗联合个性化超分割立体定向消融手术治疗109例(主要是肺癌或乳腺癌患者的)脑部病变,结果显示局部控制良好,毒性未显著增加。
目前,虽然可以考虑采用先期全身治疗替代SRS治疗或切除脑转移瘤,但需要由多学科肿瘤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权衡推迟局部治疗的利弊,并考虑SRS相对于全身治疗的最佳时机(图1和图3)。在现代中枢神经系统主动全身治疗(伴或不伴先期的SRS治疗)后有颅内放射影像学进展的患者中,优化补救性SRS治疗的递送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非侵袭性和准确区分真正的肿瘤进展和相应的管理仍然具有挑战性。
此外,在许多肿瘤组中,在脑转移定向局部治疗完成之前,保留全身治疗仍然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延迟全身治疗,或者更糟的是,由于无法阻止颅外肿瘤的进一步转移扩散和/或隐匿性脑转移的生长,局部治疗后出现新的脑转移灶。因此,结合这些模式的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图1和补充表2),可能会产生改变实践的后果,值得期待。
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缺乏随机对照试验数据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围绕临床实践中SRS治疗的测序、组合和时间表的几个未解决的问题(Box 1)。关于放射治疗反应(或耐药性)基因组预测因子的新数据的临床应用,对于这些问题的决策也有待建立。这种不确定性由于脑转移瘤患者的排除或限制入组等众所周知的问题,以及在评估实体瘤全身治疗的III期试验中缺乏针对中枢神经系统特异性结果收集的预先规范方案而更加复杂。影响临床决策的证据的不确定性需要与患者明确讨论。最后,关于这些未解问题(Box 1)的共识和高质量证据将需要进一步的多中心试验和预先指定终点的前瞻性注册研究,由学术研究联盟、专业协会和多机构合作推动。通过纳入先前关于脑转移瘤的多社会峰会提出的建议,未来调查的最佳实施和有意义的推断将成为可能。


结论
SRS已被确立为转移性脑疾病的SOC治疗范式,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在术后和术前,以及与现代全身治疗的结合的作用。ICIs和中枢神经系统活性靶向治疗的出现重申了多学科方法对脑转移瘤治疗的重要性。
然而,一些持续存在的挑战和问题仍有待回答,相应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包括(1)在整个疾病过程中可以安全使用SRS治疗的脑转移瘤的数目和大小的上限,(2)肿瘤组织学对SRS剂量和分次的重要性(表1),(3)相对于SRS治疗的最佳顺序和时间的ICIs和靶向治疗,(4)选择新辅助SRS治疗的患者的最佳方法,以及建立明确的剂量递送指南;(5)作为一个多学科团队,如何决定SRS治疗(或其他CNS导向的治疗方法)所能达到的极限,以及患者何时能从BSC中获益最多(Box 1)。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方法需要基于临床见解和伦理考虑。
尽管在获得安全和持久的控制颅内脑转移瘤方面仍然存在挑战,但SRS的使用,交付,组合方法和治疗后监测方面的进展将改善患者的预后。


声明:脑医汇旗下神外资讯、神介资讯、神内资讯、脑医咨询、Ai Brain 所发表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脑医汇及主办方、原作者等相关权利人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