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
通信作者:杨弋,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长春130021,Email:yi_yang@jlu.edu.cn;彭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北京100730,Email:pengbin3@hotmail.com;王拥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70,Email:yongjunwang@ncrcnd.org.cn
DOI:10.3760/cma.j.cn113694-20240205-00081
引用本文: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 中国头颈部动脉夹层诊治指南 2024[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24, 57(8): 813-829. DOI: 10.3760/cma.j.cn113694-20240205-00081
【摘要】头颈部动脉夹层是卒中的少见病因,准确的诊断、合理的治疗、积极的预防对其预后尤为重要。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及其脑血管病学组组织专家在《中国颈部动脉夹层诊治指南2015》的基础上,结合近9年来我国的临床实践和国内外相关的循证医学证据,制订了《中国头颈部动脉夹层诊治指南2024》。本指南对头颈部动脉夹层的诊断、治疗和预防进行了系统更新,旨在为我国头颈部动脉夹层诊治的临床实践提供循证的规范性指导。
【关键词】头颈部动脉夹层;诊断;治疗;指南

头颈部动脉夹层(cervicocranial artery dissection,CcAD)指各种原因造成颈部或颅内动脉内膜损伤撕脱,血液流入血管壁内,形成壁内血肿,使血管壁各层分离,进而造成血管狭窄、闭塞或形成夹层动脉瘤。当血肿累及内膜与中膜可造成管腔狭窄,当血肿聚集于中膜与外膜时可形成动脉瘤样扩张[1]。根据CcAD发生于颅内段和颅外段的差异,分为颅内动脉夹层(intracranial arterial dissection,IAD)和颈部动脉夹层(cervical arterial dissection,CAD);根据CAD受累动脉的不同,主要分为颈内动脉夹层(internal carotid artery dissection,ICAD)和椎动脉夹层(vertebral artery dissection,VAD)[1-2]。
CAD发生率约(2.6~3.0)/10万人年,其中ICAD发生率(2.5~3.0)/10万人年,VAD发生率(1.0~1.5)/10万人年,约13%~16%患者存在多条动脉夹层[3 4],但IAD发生率目前尚不明确。研究结果表明,颈内动脉系统的夹层多发生在颈部,而椎-基底动脉系统的夹层较多会累及颅内[5]。尽管发生率较低,但CcAD是导致青年缺血性卒中的重要病因之一。国外资料显示CAD导致的卒中约占所有缺血性卒中病因的2%,在小于45岁人群中该比例可高达8%~25%[6-8]易引起漏诊或误诊。
自2015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发布《中国颈部动脉夹层指南2015》[2]以来,CcAD诊治领域增添了丰富的循证医学证据,各国也先后发布或更新了指南和共识。为了规范CcAD诊治的临床实践,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及其脑血管病学组的专家对颈部动脉夹层指南进行了更新修订。撰写组通过复习相关研究证据,结合中国国情和临床现状,征求各方意见并充分讨论达成共识,集体制订了《中国头颈部动脉夹层诊治指南2024》,以期为神经科医生提供针对CcAD合理的诊断、治疗及预防策略[9]。

诊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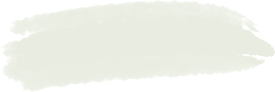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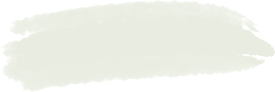
一 临床特征
经过系统详细的病史询问,结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有助于诊断CcAD。其中辅助检查具有最重要的诊断价值。
(一)年龄
CcAD多发于中青年人群。据我国的研究数据,CcAD发病平均年龄大于40岁[10-11],也有平均年龄大于50岁的报道[11-12];国外研究数据报道的CcAD发病年龄相对较小。欧美的研究结果显示,CAD患者的平均年龄在40~50岁[13-16];墨西哥研究结果显示,CAD患者平均发病年龄在35.5岁[13,17-18]。对于IAD,研究报道其发病的平均年龄更大[19-20]。由于目前对IAD的研究较少,其年龄分布情况仍存在争议。
(二)性别
CcAD多发于男性。基于我国的研究数据,男性发病比例达60%~80%[5,11-12,21-22];基于欧美人群的研究男性占53%~57%[13,23-25];基于北美的研究发现,青年人群中女性发病比例更高[26-27]。对于IAD的性别分布差异尚不明确[19,21]。
(三)危险因素和诱因
常规的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在多数CcAD患者中并不常见,但一项针对CAD的多中心队列研究(Cervical Artery Dissection and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CADISP)发现高血压是CAD的危险因素,需要重视血压的监测和管理;而高胆固醇血症、肥胖和超重则可能是CAD的保护因素[28]。通过比较CAD和IAD的危险因素发现,相较于CAD,高血压、高龄与IAD相关性更强[19,21,29]。约60%的CAD是原发的,另外40%具有相关诱因[30],如打喷嚏、剧烈咳嗽、颈部按摩、体育活动(举重、羽毛球、高尔夫球、网球及瑜伽等)均有相关报道[31-35]。纤维肌营养不良的患者更容易发生CAD[36-37]。某些特殊的解剖结构,如较长的茎突、高度迂曲的椎动脉或颈内动脉均被证实与CcAD发生相关[38-40]。头颈部血管介入手术可导致医源性的CcAD[41]。此外,遗传因素可能也在CcAD的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血管性埃勒斯 丹洛斯综合征、马凡综合征、成骨不全症和洛伊迪茨综合征在内的多种单基因结缔组织疾病被认为与CcAD相关[42-43]。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C677T多态性和Rs9349379[G]等位基因(PHACTR1)突变,也被证明会增加CAD发病风险[44-45]。目前研究暂缺少对IAD特殊诱因的探索。
(四)临床症状
CcAD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头痛、颈痛及继发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是最常见的表现[23-46]。卒中是CcAD最为常见的表现,多数患者表现为缺血性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13-15,21];少数患者可以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在CAD中约占1%[13,15,27-47],在IAD中约占3%[19]。也有部分患者无明显临床症状,在CAD中约占6%[48],在IAD则无相应报道。
1.疼痛:CcAD形成后可导致局部的疼痛。疼痛的部位根据夹层位置不同而有所区别,可表现为单侧或双侧颈痛和(或)头痛,约有53%的CcAD患者以头痛为首发症状[49]。IAD多伴随有头痛,颈痛相对少见;而对于CAD,头痛及颈部疼痛均可出现。发生于颈内动脉系统的夹层引起的头痛多累及颞部,其次为额部,也有报道会累及颈部及眼眶;而颈项部及后枕部疼痛则多提示椎基底动脉系统动脉夹层[11,50]。疼痛的性质和程度也不尽相同,抽痛、刺痛或搏动性疼痛均可出现,椎基底动脉系统夹层和前循环相比,其疼痛发生的比例和严重程度均更高[11,49]。椎动脉夹层患者还可伴随畏声、畏光等症状[51]。若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头痛程度更为剧烈,部分患者伴有搏动性耳鸣[11,52]。
2.神经功能缺损症状:神经功能缺损症状与其他病因所致的脑血管病的症状无差异。累及前循环者可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感觉减退、口角歪斜、黑矇等缺血症状[53-54]。累及后循环者则可出现眩晕、耳鸣、视野缺损等症状,严重者甚至昏迷[54-56]。缺血症状通常出现在头颈部疼痛后的数分钟至数周。与ICAD相比,VAD更易发生缺血事件[57],VAD的颅内段病变与颅外段相比,更容易引起缺血事件及神经功能缺损症状[58]。此外,初次发病的CAD比复发者更易引起神经功能缺损症状[59]。当VAD累及脊髓供血动脉时,根据受累部位不同可出现单侧或者双侧的肢体无力、麻木等脊髓缺血症状[48,60-62]。
3.其他症状:颈神经根性疼痛、搏动性耳鸣等是CcAD相对少见的症状[63]。搏动性耳鸣多见于外伤导致的CcAD[64-65]。VAD可压迫颈神经根,引起颈、肩部及单侧肢体的疼痛及活动受限等症状[66-68]。
(五)临床体征
CcAD的临床体征与其他病因所致卒中的神经系统局灶或全面功能障碍体征无差异。然而,结合头颈部动脉的解剖位置与特点,有些重要体征应该关注。
1.霍纳综合征:霍纳综合征对ICAD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约有44.4%的ICAD出现了霍纳综合征。由于颈交感神经纤维大部分分布于颈内动脉,而少部分(支配汗腺)分布于颈外动脉,因此ICAD患者表现为瞳孔缩小、眼睑下垂及眼球轻度内陷,但不伴面部无汗的不完全霍纳综合征[23,69]。据统计,VAD患者也有小部分出现了霍纳综合征,其比例仅为7.6%[57,70],是由于损伤了延髓交感神经下行纤维所致。
2.脑神经损害:CcAD压迫周围结构或引起后循环缺血,可出现多组脑神经损害体征。后组脑神经受损多见,以舌下神经最常见,舌咽神经、迷走神经次之。此外,动眼神经、三叉神经、面神经受累偶有报道[48]。
3.脊髓缺血体征:累及椎动脉的CcAD可影响脊髓血供,引起脊髓后动脉缺血症候群,表现为单侧或者双侧不同程度的节段性肌力减退、深浅感觉障碍及感觉性共济失调等。严重者甚至出现脊髓半切综合征[48,60-61]。
4.脑膜刺激征:CcAD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者可表现为颈项强直、克尼格征、布鲁氏征等脑膜刺激征。蛛网膜下腔出血多见于IAD[71-72]。
5.颈部血管杂音:CAD导致动脉狭窄,可闻及收缩期血管杂音。
二 辅助检查
CcAD的诊断依赖于影像学观察到的“血管狭窄”“壁内血肿”“双腔征”“内膜瓣”“夹层动脉瘤”等征象[71]。CcAD的辅助检查包括头颈部动脉超声、电子计算机体层扫描(computerized tomography,C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此外,影像学检查还能够观察到CcAD引起的继发改变,如脑梗死、蛛网膜下腔出血、动脉瘤形成及动脉狭窄和闭塞等。近年来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HR MRI)管壁成像技术进一步发展,为CcAD的诊断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73]。
(一)头颈部血管超声
颈部动脉超声检查具有无创、费用低、操作简便、易普及推广等优点。对于CAD,通过连续多普勒与脉冲多普勒的结合,既可以观察到管腔和管壁结构,发现“双腔征”“内膜瓣”“壁内血肿”等直接征象(图1),还可以监测血流速度、动脉搏动指数、血管狭窄闭塞等间接征象。经颅多普勒超声可以通过脉冲多普勒监测颅内大血管血流,获得血管狭窄等信息。超声检查对血管闭塞的敏感度达到100%,对中重度狭窄的敏感度为95.7%,但在轻度狭窄时敏感度降至40%[74]。将颈部血管超声和经颅多普勒技术结合有助于提高颈部动脉超声诊断的准确性。而对于IAD,由于颅骨对声波的阻断,经颅多普勒技术仅能反映颅内动脉狭窄情况,缺乏对管腔管壁结构直观的观察。头颈部血管超声检查结果的准确性与检查者的经验、病变的严重程度及血管病变的部位密切相关,在临床上用于筛查或随访评估,IAD的诊断需要结合其他检查手段[75]。

(二)CT
CT平扫可用于观察脑梗死、蛛网膜下腔出血等CcAD引起的间接改变。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用于观察血管管腔结构,具有空间分辨率高、无创、应用广泛等优势。由于不受颅骨限制,CTA对颅内颅外的动脉夹层均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由于使用造影剂来观察血管,CTA与磁共振血管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相比,在管腔内结构的显示方面更具优势,能够发现“双腔征”(图2)“内膜瓣”“夹层动脉瘤”“线样征”等征象,对“壁内血肿”也有一定的观察能力[76-78]。椎动脉血管较为纤细且靠近骨骼结构,CTA观察VAD效果比MRA更好[79-80]。
CT的缺陷主要在于其放射线损伤,CTA还需要用碘造影剂,应注意过敏风险,此外CT检查容易受颅底或牙齿骨质伪影的影响。因而对于肾功能不全、造影剂过敏者、妊娠妇女、儿童等应谨慎使用。

(三)MRI
MRI检查由于不受骨性结构的干扰,能够对颅内结构进行有效的观察,在CcAD的评估中具有重要价值。磁共振T1加权像(T1 weighted imaging,T1WI)、T2加权像(T2 weighted imaging,T2WI)、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等对动脉夹层引起的卒中病灶具有良好的成像效果。MRA不需要注射造影剂,通过流空效应能够对颅内动脉管腔内结构进行较为准确的观察。
在发病48h以内壁内血肿的成分主要为氧合血红蛋白,在T1WI、T2WI上均呈等信号;发病48~72h,血肿主要成分转化为脱氧血红蛋白,在T1WI、T2WI上均呈高信号[53,81];高信号可以维持多达数月,之后逐步消退为等信号。HR MRI的管壁成像技术能够有效抑制血管内流动的血液信号,可清晰地显示头颈部动脉的“壁内血肿”[29,82-84],极大地提升了对CcAD的观察能力(图3),目前已经成为诊断CcAD的重要手段[85-86]。此外,HR-MRI能够观察到新月形高信号的壁内血肿,利于CcAD与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炎等其他原因引起的动脉狭窄相鉴别。有研究报道HR MRI管壁成像对于椎动脉IAD的诊断能力优于DSA[87-88]。另有研究报道,HR MRI管壁成像与DSA相比,对IAD的诊断与临床具有更高的一致性(90.6%比53.1%)[87]。HR MRI管壁成像对CcAD壁内血肿直观展示也能够指导对血管内治疗指征的把控[89]。此外,HR MRI显示的壁内血肿信号强度变化对动脉夹层的扩大及转归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壁内血肿与颈后肌相对信号强度比值的变化对夹层自发性愈合可能有预测意义[90-92],可用于IAD的随访监测[93]。另有研究报道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序列对IAD也有一定的诊断价值[94]。鉴于MRI无创、便利等特点及HR MRI对管壁结构良好的观察效果,MRI有望成为CcAD最具潜力和诊断效力的检查手段[87-88]。
MRI的劣势主要在于价格昂贵、设备要求高、检查时间长、存在检查禁忌(如心脏起搏器、体内金属置入、幽闭恐惧)等,在上述情况下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应用。

(四)DSA
长期以来,DSA曾被公认为诊断CcAD的“金标准”。通过动态、实时、多角度的观察,DSA对血管管腔内结构提供了最直接、准确的观测,还能对血流代偿、侧支循环等情况进行评价。由于不受颅骨的限制,DSA观察颅内及颅外段动脉夹层的效果均佳。动脉夹层在DSA上的表现通常是“血管串珠样狭窄”“血管闭塞”“动脉瘤”“真假腔”“内膜瓣”(图4)等,也可以表现为“鼠尾征”“线样征”“火焰征”等征象。
DSA检查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价格昂贵、费时、对设备要求高及有创等。此外,由于仅对管腔内进行观测,DSA缺少对血管管壁结构的评估,在动脉管径正常时有漏诊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诊断的准确性,在诊断动脉夹层时并非常规使用。在无创检查技术不能确诊或需要进行介入治疗的情况下,可考虑DSA检查。

三 其他诊断方法
(一)肾动脉血管检查
纤维肌营养不良是一种以中小动脉非动脉粥样硬化性平滑肌纤维和弹性组织发育异常为特征的全身性血管疾病,可形成动脉夹层和动脉瘤,常累及颈部动脉及肾动脉,偶累及颅内动脉[95]。据研究报道19%的纤维肌营养不良患者合并有CAD[96]。因而建议对具有高血压病史且累及多血管的、反复出现的CcAD患者进行肾动脉检查,作为纤维肌营养不良的排查项目。
(二)基因检测
结缔组织异常被认为是发生CcAD的重要原因之一[16]。约有1%的CAD被证明与单基因结缔组织疾病有关,包括血管性埃勒斯 丹洛斯综合征(COL3A1基因)、马凡综合征(原纤维蛋白1基因)、成骨不全症(COL1A1或COL1A2基因)和洛伊迪茨综合征(TGFBR1、TGFBR2、TFFB2或SMAD3基因)等[42]。因而,对于反复发作或有单基因结缔组织疾病家族史的夹层患者建议行基因检测。
四 CcAD影像鉴别诊断
(一)动脉粥样硬化
与CcAD不同(图5A),动脉粥样硬化多见于高龄人群,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可伴或不伴头晕、黑矇等脑缺血症状,合并TIA及缺血性卒中时可伴有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头颈部血管超声、CTA、MRA、DSA等影像学检查可观察到“血管狭窄”“斑块形成”等征象。通过HR MRI(图5B)能更清晰地观察斑块重构类型、斑块负荷、内部出血、钙化等特征[97-98]。

(二)血管炎
血管炎发病前可有前驱感染史或自身免疫疾病病史。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可急性抑或慢性起病,可表现为头痛、头晕、精神症状、记忆力障碍等,也可表现为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影像学检查可见广泛的血管狭窄、管壁增厚,HR MRI可见特征性的动脉管壁“环形强化”(图5C)[98-99]。
推荐意见:(1)CcAD是缺血性卒中的少见病因,却是青年卒中的常见病因,建议对年轻尤其是缺乏常见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缺血性卒中患者进行CcAD筛查(Ⅰ级推荐,C级证据)。(2)目前尚无评估CcAD的单一“金标准”,对于发生缺血性卒中、TIA的疑似CcAD的患者,应首选头颈动脉超声、CT、MRI等无创性检查进行诊断评估(Ⅰ级推荐,C级证据)。(3)在急性缺血性卒中、TIA患者中,尤其是中青年患者,颈部血管超声可以作为CAD的筛查及复查随访手段(Ⅰ级推荐,C级证据)。(4)对于IAD,应根据临床实际需要选择CT、DSA、MRI及HR MRI等检查进行综合评估(Ⅱ级推荐,C级证据)。(5)对于IAD,HR MRI与其他检查手段相比可能具有更好的成像效果(Ⅲ级推荐,C级证据)。

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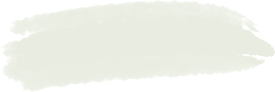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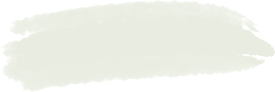
国内外近10年来的研究结果提示,临床治疗CcAD主要是针对CcAD导致的不同临床病变,包括急性缺血性卒中、夹层动脉瘤及蛛网膜下腔出血等来开展的。鉴于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目前临床治疗方法均应参照相关疾病的基本治疗原则,如CcAD导致缺血性卒中的急性期治疗和二级预防策略原则上同现行指南[9,100-101]。本指南主要针对临床医师重点关注的治疗措施在本病中应用的问题进行阐述和推荐。
一 CcAD相关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再灌注治疗
(一)静脉溶栓
静脉溶栓是治疗缺血性卒中的有效方法。当CcAD导致缺血性卒中事件时,CcAD可能伴随动脉血管壁破坏、血管内膜下血肿形成,静脉溶栓可能会加重血管损伤,增加出血风险。目前缺乏随机对照研究对CcAD导致的缺血性卒中患者溶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分析。
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CAD引起急性缺血性卒中并接受静脉或动脉溶栓治疗的患者180例,平均NIHSS评分16分,67%接受重组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ecombinant plasminogen activator,rt PA)静脉溶栓,33%接受rt PA动脉溶栓,总体颅内出血发生率3.1%,总体病死率8.1%,预后良好患者比例41%,与其他病因导致的卒中相比,接受溶栓治疗的CAD患者安全性及预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提示溶栓治疗对CAD患者具有较好的安全性[102]。2016年一项针对静脉溶栓治疗CAD引起缺血性卒中的荟萃分析纳入了10项研究[103],共纳入846例CAD患者(其中174例接受了静脉rt PA治疗),结果表明对于CAD引起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而言,静脉溶栓治疗与其他原因引起的缺血性卒中的静脉溶栓治疗效果相当,也未增加症状性颅内出血的风险,因此,CAD所致的缺血性卒中患者并非静脉溶栓的禁忌,不过仍需要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进行证实。
对IAD合并卒中患者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研究相对较少。一项单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纳入了10例IAD导致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104],其中5例患者接受了静脉rt-PA治疗。IAD的位置分布于颈内动脉远端、大脑中动脉M1段、大脑前动脉A2段以及基底动脉。静脉溶栓后没有出现蛛网膜下腔出血或症状性颅内出血,1例患者出现了无症状性出血转化,2例患者在发病7d内因脑梗死所致的脑水肿而死亡,其他3例患者预后良好[3个月随访中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1分],静脉溶栓治疗似乎相对安全,遗憾的是病例太少,仍需更多研究来评估其疗效和安全性。2021年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144例由于颈内动脉颅外段夹层所致血管串联闭塞的急性卒中患者,其中94例(65.3%)在急诊机械取栓治疗(mechanical thrombectomy,MT)前接受静脉rt PA治疗。研究发现在MT前接受静脉溶栓治疗与更好的临床结果显著相关(P=0.004)。MT前接受静脉溶栓治疗也与较高的再灌注成功率(83.0%比64.0%,aOR=2.63;95%CI1.12~6.15,P=0.025)和较低的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4.3%比14.8%,aOR=0.21;95%CI0.05~0.80)相关。因此,与单独MT相比,颈内动脉颅外段夹层相关的串联闭塞在术前进行静脉溶栓治疗是安全的,并可改善90d的功能预后[105]。
在目前多个国内外急性缺血性卒中指南中的静脉溶栓治疗部分均未将CcAD排除在外[9],不过仍需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来进一步证实CcAD相关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二)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
目前尚无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CcAD相关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CAD患者是否需要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主要是参照急性大血管闭塞患者现有的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标准[106],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策略包括支架取栓治疗、血栓抽吸治疗、动脉溶栓、急性期血管成形术及支架植入术等。一项关于CAD并发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早期血管内治疗的荟萃分析(纳入193例接受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59例接受内科治疗)结果表明,与内科治疗相比,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的患者90d良好预后(mRS评分≥2分)占比更多(41.5%比62.9%,P=0.006),而两组之间症状性颅内出血(5.9%比4.2%,P=0.60)和病死率(6.3%比8.6%,P=0.59)均没有显著差异[107]。对于CAD相关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选择静脉溶栓治疗还是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59例接受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患者和139例单纯静脉溶栓治疗的CAD相关急性卒中患者,结果表明两组3个月良好预后(mRS评分≤2分)占比分别为71.2%(95%CI58.4%~81.3%)和53.4%(95%CI44.9%~61.7%),即3个月随访时,接受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的患者比静脉溶栓治疗的患者获得良好预后(mRS评分≤2分)可能性更大,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合并OR=2.157,95%CI1.117~4.168,P=0.031);在安全性方面,两组之间症状性颅内出血和病死率均无显著差异(合并OR=2.765,95%CI0.170~42.026,P>0.05;合并OR=2.373,95%CI0.571~9.855,P=0.407)[108]。
但一项汇总了前瞻性多中心观察研究队列(Endovascular Treatment in Ischemic Stroke,
ETIS)和国际登记研究(Thrombectomy in Tandem Lesions,TITAN)的研究共纳入136例因CAD导致串联闭塞的患者,其中65例(47.8%)接受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71例(52.2%)接受内科标准化治疗,两组之间的90d良好预后(mRS评分≤2分)占比(61.4%比54.3%,校正OR=0.84,95%CI0.58~1.22,P=0.41)和症状性出血并发症(5.6%比10.8%,校正OR=1.59,95%CI0.79~3.17,P=0.19)均未见明显差异[109]。基于上述研究,针对CAD相关的急性缺血性卒中进行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总体是安全有效的,但仍需要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深入探索。针对IAD患者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的相关研究较少。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7例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大脑中动脉夹层引起的急性完全闭塞患者,3个月随访良好预后(mRS评分≤2分)占比为83.8%,3个月的卒中复发率为1.6%。由于该研究是回顾性的病例分析,因此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IAD相关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然未知,需要更严谨的临床研究来进一步探索[110]。
推荐意见:(1)目前缺乏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评估在CcAD所致缺血性卒中患者中开展静脉溶栓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需积极开展临床研究。现有证据显示在发病4.5h内运用静脉rt-PA治疗CAD所致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是安全的(Ⅱ级推荐,C级证据)。(2)对CAD相关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进行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总体是安全和有效的,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Ⅲ级推荐,C级证据)。(3)对IAD相关的急性缺血性卒中进行再灌注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然未知(Ⅲ级推荐,C级证据)。
二 抗血小板/抗凝治疗
多数缺血性卒中发生在CcAD的初始症状出现后不久,如果进行及时干预可以预防卒中事件的发生或进展。CcAD导致潜在的缺血性卒中发生机制包括夹层局部血栓形成引起的动脉 动脉栓塞、狭窄造成的血管灌注不足以及内膜瓣阻塞夹层血管和(或)其分支,其中血栓 栓塞机制被认为起主要作用,因此,抗栓治疗是预防夹层所致缺血性卒中的重要治疗方法[111-112]。
CAD卒中研究(The Cervical Artery Dissection in Stroke Study,CADISS)是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比较发病7d内CAD应用抗血小板和抗凝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并且从2012年到2019年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结果[112]。在CADISS研究中,抗血小板治疗使用药物包括单用阿司匹林、双嘧达莫、氯吡格雷或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抗凝药物方案包括低分子肝素和华法林,肝素应用后使用华法林持续3个月,维持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在2~3。结果发现在有症状的CAD患者中,3个月总卒中发生率在抗血小板治疗和抗凝治疗组之间未见差异(4.0%比4.0%,P=0.87),抗凝组发生l例蛛网膜下腔出血而抗血小板组无出血性事件发生[14]。瑞士的一项多中心、随机、开放标签、非劣效性试验(Aspirinversus Anticoagulation in Cervical Artery Dissection,TREAT-CAD)分析了173例CAD患者,分为阿司匹林组(300mg每日1次,91例)或维生素K拮抗剂组(苯丙香豆素或醋硝香豆素或华法林,目标INR2.0~3.0,82例),治疗持续90d,主要复合终点包括临床结局(卒中复发、出血或死亡)和MRI结局(出现新发缺血或颅内出血),结果提示阿司匹林组91例患者中有21例(23%)出现主要终点事件,维生素K拮抗剂组的82例患者中有12例(15%)出现主要终点事件[绝对偏差8%(95%CI-4~21),非劣效性P=0.55]。因此,与维生素K拮抗剂相比,阿司匹林在治疗CAD方面未显示出非劣效性[113]。2022年对15项试验的2064例CAD患者进行抗血小板和抗凝治疗疗效比较的荟萃分析发现,纳入444例患者(来自CADISS和TREAT CAD研究)中抗血小板和抗凝治疗后首次卒中发生率有明显差异(4.42%比0.46%,OR=6.97,95%CI1.25~38.83,P=0.03),而两组之间3个月的病死率、卒中复发以及出血方面均未见明显差异,虽然该研究发现在CAD导致的首次缺血性卒中患者中,抗凝治疗优于抗血小板治疗,但考虑到不同研究的药物应用的剂量、频次以及给药依从性等混杂效应的调整不完全,仍需要深入探索[114]。2024年一项国际多中心观察性研究(Stroke Prevention in Cervical Artery Dissection,STOP CAD)的结果公布,该研究共纳入3636例CAD患者(2453例接受抗血小板治疗,402例接受抗凝治疗,781例联合抗血小板和抗凝治疗)。在预防缺血性卒中方面,与抗血小板治疗相比,抗凝治疗在30d(调整后HR=0.71,95%CI0.45~1.12,P=0.145)和180d(调整后HR=0.80,95%CI0.28~2.24,P=0.670)的缺血性卒中发生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与抗凝治疗相关的主要出血在180d时显著增加(HR=5.56,95%CI1.53~20.13,P=0.009)。亚组分析结果表明,在接受抗凝治疗的CAD患者中,尤其是CAD引起动脉闭塞的患者中,抗凝治疗在预防缺血性卒中方面疗效显著(HR=0.40,95%CI0.18~0.88,P=0.009)。研究指出,鉴于绝大多数缺血性卒中事件发生在夹层确诊的最初30d内,如果最初选择抗凝治疗,那么在30d后转换至抗血小板治疗以降低出血风险是合理的。由于该研究是回顾性研究,因此,仍需要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对抗栓治疗的疗程和停药时机进行探索[115]。对于6个月后是否继续抗血小板或抗凝治疗,目前仍然存在争议。一项研究对来自意大利年轻成年人CAD卒中研究项目(The Italian Projecton Stroke in Young Adults Cervical Artery Dissection,IPSYS-CeAD)的CAD患者进行随访,比较了6个月后停用和继续服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药物的缺血性卒中发生风险,发现6个月时停用抗栓药物的患者(201例)与继续接受抗栓治疗的患者(201例)的缺血性卒中或TIA发生率相当[4.5%比5.0%,P(logrank检验)=0.526],说明6个月后停止抗血小板或抗凝治疗似乎不会增加随访期间缺血性卒中发生风险[116]。另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CAD患者接受抗血小板或抗凝单一治疗(22例)以及二者联合治疗的有效性,如随访期内出现血管再通则停药,其他患者持续治疗至6个月,治疗结束后联合治疗组功能性再通发生率(71.4%)比单一治疗组(36.4%)高1.96倍(P=0.021)。因此,抗血小板和抗凝联合治疗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使CAD获得更有效再通,且相较于单独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药物未增加不良事件发生的风险[117]。据此,总结CAD的抗栓治疗策略供临床实践参考:对于存在CAD所致血管严重狭窄/闭塞或管腔内血栓形成等高危因素且出血风险较小的患者更适合抗凝治疗;而出血风险较高的患者更适合抗血小板治疗[106]。但仍然需要更多拥有良好设计的临床研究带来更充足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回顾性研究还比较了CAD患者使用抗血小板药物、传统抗凝药和新型口服抗凝药(novel oral anticoagulants,NOACs)的治疗效果。在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中[118],NOACs组(达比加群、利伐沙班或阿哌沙班)39例、传统抗凝组(华法林或治疗剂量的低分子肝素)70例和抗血小板药物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阿司匹林/缓释双嘧达莫)40例在治疗3~6个月结束后随访结果显示各组CAD患者的卒中复发率未见明显差异(P=0.822),与NOACs组(0)和抗血小板药物组(2.5%)相比,传统抗凝药组(11.4%)发生了更多的大出血事件(P=0.034)。另外,一项单中心小样本的队列研究纳入了CAD导致卒中的患者,其中6例接受NOACs治疗(3例服用达比加群,3例服用利伐沙班),62例接受维生素K拮抗剂治疗,6个月治疗结束随访时,5/6接受NOACs和54.8%(34/62)接受维生素K拮抗剂治疗的患者血管完全再通,并且所有服用NOACs的患者预后良好(mRS评分≤1分)且无颅内出血发生,而维生素K拮抗剂治疗组48例(77%)患者预后良好(mRS评分≤1分),1例(1.7%)发生了颅内出血[119]。一项病例回顾和系统综述报道了49例接受NOACs的CAD患者[120],6个月治疗结束随访时发现27例(55%)患者实现血管再通,2例(4%)出现卒中复发,无一例发生颅内出血。上述研究支持NOACs作为CAD患者抗凝治疗的替代药物,但目前尚缺乏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进行深入探索。
针对IAD的抗栓治疗策略,国内外临床研究较少。2017年一项比较抗血小板治疗、抗凝治疗和联合治疗策略对370例CcAD患者(76例IAD患者和294例CAD患者)疗效的回顾性研究结果表明,对于76例IAD的卒中患者(63.1%抗血小板治疗,19.7%抗凝治疗,14.5%联合治疗),3组不良预后(mRS评分>2分)的比例分别为4.2%、7.1%和9.1%,出血事件的比例分别为2.1%、7.1%和9.1%。结果表明,不同亚组IAD患者抗栓治疗方式和缺血/出血事件以及临床预后没有显著差异[121]。对于预防IAD卒中复发的治疗策略,仍然需要更多临床研究支持。
推荐意见:(1)推荐在CAD形成的急性期,使用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Ⅰ级推荐,B级证据)。在降低CAD患者卒中发生风险方面,抗凝治疗优于抗血小板治疗,但需注意监测出血风险(Ⅱ级推荐,B级证据)。对于存在CAD所致血管严重狭窄/闭塞或管腔内血栓形成等高危因素且出血风险较小的患者更适合抗凝治疗;而出血风险较高的患者更适合抗血小板治疗(Ⅲ级推荐,C级证据)。抗血小板和抗凝联合治疗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使CAD获得血管再通(Ⅲ级推荐,C级证据)。临床上可结合具体情况进行选择。(2)由于缺乏在IAD患者中抗栓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结合临床实践,推荐在IAD导致的缺血性卒中或TIA患者中使用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但需注意监测出血风险(Ⅲ级推荐,C级证据)。(3)目前缺乏足够的证据对抗凝治疗的疗程和药品种类进行推荐。对于CAD导致缺血性卒中或TIA患者,抗凝治疗至少3~6个月以预防卒中复发或TIA(Ⅱ级推荐,B级证据)。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或华法林都是可选择的治疗药物;肝素治疗时维持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达到50~70s,华法林抗凝治疗时维持INR2~3(Ⅱ级推荐,C级证据)。NOACs也可作为CAD患者抗凝治疗的替代药物,仍需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证实(Ⅲ级推荐,C级证据)。临床上可结合具体情况选择。(4)目前缺乏足够的证据对抗血小板治疗的疗程和种类进行推荐。对于CAD导致缺血性卒中或TIA患者,抗血小板治疗至少3~6个月以预防卒中复发或TIA(Ⅱ级推荐,B级证据)。可单独应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双嘧达莫;也可选择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或阿司匹林联合双嘧达莫(Ⅱ级推荐,B级证据)。临床上可结合具体情况选择。
三 介入治疗或手术治疗
血管内介入治疗或手术治疗可以作为CcAD相关卒中发生/复发的治疗手段。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分析了接受血管内介入治疗的44例ICAD患者(颅外段夹层28例,颅内段夹层16例)。结果表明83.7%的患者出院时症状改善(mRS评分≤2分),并且所有患者在随访期间(平均19.2个月)未出现新发卒中,说明血管内介入治疗ICAD总体是有效的,尤其是对药物治疗无反应的ICAD患者应考虑介入治疗[122]。另外,一项系统综述纳入了140例接受血管内介入治疗的CAD患者(153条发生夹层的血管),其中引起CAD的病因包括外伤性(48%)、自发性(37%)和医源性(16%),总体平均临床随访时间为17.7个月(1~72个月),结果发现血管内介入治疗技术成功率达99%且总体是有效的,夹层动脉瘤的闭塞率达98.4%,只有2例患者出现缺血性卒中(1.4%)和2例患者出现手术并发症(1.3%)[123]。因此,对于CcAD相关缺血性卒中患者,如果在积极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仍有缺血性事件发生,可考虑血管内介入治疗或手术治疗作为卒中预防手段,但仍需要前瞻性的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证实。
值得关注的是,颅内外医源性血管夹层是一种与血管内治疗相关的手术并发症。来自瑞士的一项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后出现的医源性夹层[41],在866例接受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的患者中,18例(2%)发生了医源性夹层(44%为女性,中位年龄64岁),其中颅外15例(占83%),颅内3例(占17%)。在医源性CcAD中,5例(28%)引起重度血管狭窄,3例(17%)为中度血管狭窄,5例(28%)为轻度血管狭窄,5例(28%)未导致明显狭窄,其中8例(44%,5例重度狭窄,1例中度狭窄,1例轻度狭窄和1例无狭窄患者)患者接受了支架植入治疗医源性夹层。24h随访时未发现新发的卒中病变。一项病例报道描述了2例患者通过支架植入术治疗颅内动脉医源性夹层,均预后良好[124];另一项病例研究报道通过支架植入术治疗医源性CAD(3例ICAD和3例VAD),6例患者在放置支架后血流均得到恢复,中期随访(6~8个月)结果显示所有患者支架内血流通畅[125]。因此,针对医源性CcAD,血管内支架植入治疗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安全性,但仍需大样本量的临床试验结果证实。
CcAD形成夹层动脉瘤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时,可选用的治疗方法包括血管内介入治疗(夹层动脉近端闭塞、动脉瘤栓塞)和手术治疗(动脉瘤夹闭)。一项回顾性病例研究分析了20例VAD夹层动脉瘤破裂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18例接受动脉瘤栓塞治疗,2例接受保守治疗),动脉瘤栓塞治疗的18例患者夹层动脉瘤均成功闭塞,实现血管重建,未接受动脉瘤栓塞治疗的患者均死于再出血[126]。同样地,另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12例接受栓塞治疗的椎动脉和小脑后下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例,其中10例患者恢复良好(mRS评分≤2分)且无复发[127]。一项回顾性病例研究评估了41例接受血管重建治疗的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患者,随访(随访时间21.5个月)发现70.7%的患者预后良好(mRS评分≤2分)[128]。因此对于CcAD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应当尽早接受手术治疗或血管内介入治疗,临床需结合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推荐意见:(1)在使用最佳药物治疗后仍出现卒中复发事件时,可考虑血管内介入治疗或手术治疗作为CAD患者的治疗手段(Ⅱ级推荐,B级证据)。血管内介入治疗或手术治疗IAD导致缺血性卒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Ⅲ级推荐,C级证据)。(2)支架植入术治疗医源性CcAD是可行的,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Ⅲ级推荐,C级证据)。(3)对于IAD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建议尽早进行外科手术治疗或血管内治疗(Ⅲ级推荐,B级证据)。

预防与预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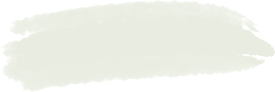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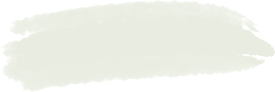
针对CAD的预防,控制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可减少CAD的发生,但缺乏针对性的临床研究。高血压是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但目前缺乏通过降压以减少CAD动脉管壁损伤的证据。他汀类药物在缺血性卒中的二级预防中至关重要,在CAD导致的卒中患者中应用他汀类药物可能会改善患者预后,但不能预防卒中复发和心血管事件[129]。对于血压和血脂异常的控制,应结合患者具体情况,权衡利弊,进行个体化干预。遗传因素在部分CcAD的发生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反复发作或有单基因结缔组织疾病家族史的CcAD患者建议进行基因检测,但不推荐常规进行基因检测[106]。针对偏头痛,尤其是不伴有先兆的偏头痛患者,应尽早结合患者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明确其是否与CAD相关[130-131]。目前仍缺少IAD预防的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索。诱发因素在CcAD发生中不容忽视,如不适当的机械外力是发生CcAD的诱因,应谨慎进行颈部按摩推拿、警惕颈椎外伤等机械触发事件[32,35,132-133];应尽量规避介入手术带来的医源性损伤,以期达到预防CcAD发生的目的[41,134]。
多数CAD患者的预后较好,较低[135]。TREAT CAD研究分析了病死率及复发率173例CAD患者,97.1%(168/173)的CAD患者3个月预后良好(mRS评分≤2分),3个月随访时有2.9%(5/173)的患者CAD复发[113]。一项纳入2064例CAD患者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76.5%(614/803)的CAD患者6个月预后良好(mRS评分≤2分),短期(≤3个月)和长期(>3个月)随访期病死率分别为0.2%和1.4%[114]。另一项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展的队列研究纳入177例CAD患者,对其中51例患者进行了影像学(CTA/MRI/MRA)分析,结果表明CAD的自发再通率高达58.8%,再通的平均时间为4.7个月[136]。IAD的预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临床症状,与缺血性卒中相比,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的IAD患者临床结局更差、病死率更高[137]。一项队列研究共计纳入了113例IAD患者,结果发现76.6%的IAD患者90d临床结局良好(mRS评分≤2分),40.0%的IAD患者在随访时(中位时间26周)表现为完全再通或血流动力学显著恢复[138]。
推荐意见:(1)应开展评估和干预CcAD的危险因素,以提前预防CcAD的发生(Ⅲ级推荐,C级证据)。(2)避免CcAD诱发因素,如创伤及医源性血管损伤,以减少或避免夹层的发生(Ⅲ级推荐,C级证据)。
执笔
杨弋(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彭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靳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郭珍妮(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委员与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欣(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王玉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王延江(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王拥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王佳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王丽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田成林(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朱遂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朱以诚(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朱武生(东部战区总医院)、刘军(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刘鸣(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尊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刘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刘俊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孙伟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孙钦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李子孝(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李新(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李刚(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杨弋(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肖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吴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吴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何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何志义(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汪昕(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汪银洲(福建省立医院)、张通(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张杰文(河南省人民医院)、张宝荣(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陆正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陈会生(北部战区总医院)、武剑(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范玉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林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孟强(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赵钢(西北大学医学院)、赵性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胡文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胡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施福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骆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秦超(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夏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徐运(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徐安定(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殷小平(九江学院附属医院)、郭力(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焉传祝(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黄旭升(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戚晓昆(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崔丽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彭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董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韩建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程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傅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曾进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蒲传强(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楼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蔡晓杰(北京医院)、管阳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滕军放(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
声明:脑医汇旗下神外资讯、神介资讯、神内资讯、脑医咨询、Ai Brain 所发表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脑医汇及主办方、原作者等相关权利人所有。
投稿邮箱:NAOYIHUI@163.com
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裁切、录制等。经许可授权使用,亦须注明来源。欢迎转发、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