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神外资讯:何教授,意识障碍是一个新兴且综合性的学科,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意识障碍学科和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意识障碍外科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在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取得的突出成果是什么?
何江弘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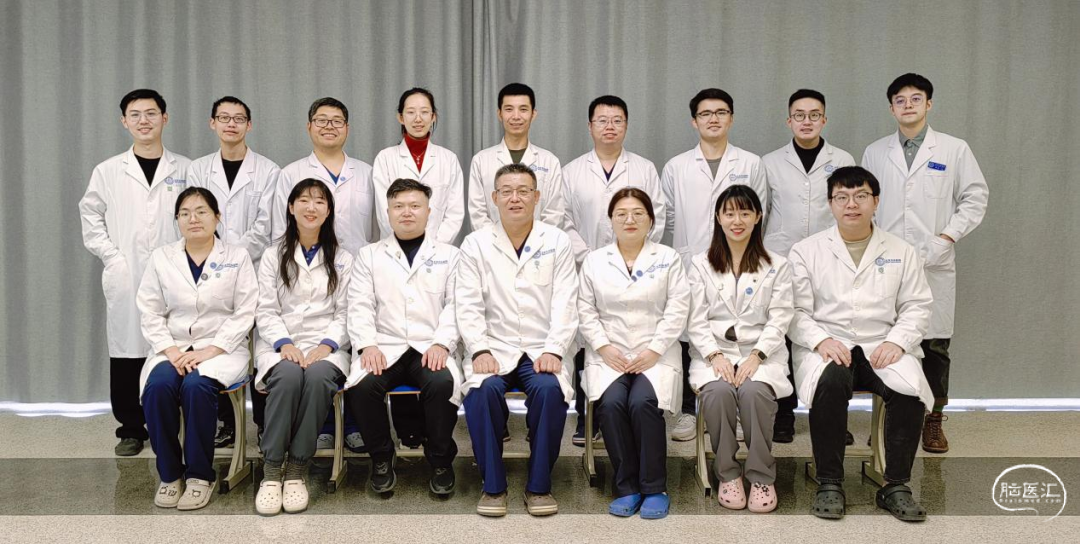
02
神外资讯:您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学术排名非常高,能否谈谈您对此的看法?这对您的研究工作有何影响?
何江弘教授:
03
神外资讯:您的“Long-term functional outcomes improved with deep brain stim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研究揭示了脑深部电刺激术(DBS)在改善慢性意识障碍患者长期功能结局方面的显著效果。在您看来,这一发现对于慢性意识障碍治疗领域的未来发展有何深远影响?它是否能够开启全新的治疗路径或促进多学科间的深度合作?
何江弘教授:
04
神外资讯:能否请您进一步展开讨论一下30~40%预后较好的患者,他们在术前评测方面有什么标准?
何江弘教授:

05
神外资讯:您作为主要负责人,在“智能机器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将脑机接口技术与康复机器人相结合,旨在帮助意识障碍患者实现最大限度的功能康复。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跨领域合作的创新性和未来潜力?以及您认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何江弘教授:

06
神外资讯:您牵头制定了中国专家共识2部,能否谈谈这些专家共识的制定和推广如何促进了行业内观念的更新和变革?您对这一领域中国第一部指南有怎样的期待呢?此外,您对意识障碍领域的未来有何展望?
何江弘教授:
![]()
专家介绍
何江弘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天坛医院意识障碍外科主任。从事昏迷及植物状态促醒治疗。认知与意识障碍患者隐匿意识的多模态检测与评定;无创神经调控(TMS,tDCS等)治疗方案与评定,外科促醒手术及程控技术。基于检测的精准术后程控;残存意识与运动意图的人机交互输出。在“昏迷与意识障碍领域”近5年Scholarly学术排名中,亚太地区排第一,全球排第八
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等课题。牵头制定中国专家共识2部。荣获北京医学科技奖二等奖(排名第一)
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学分会意识障碍学组主任委员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神经生理学组副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分会委员
![]()
声明:脑医汇旗下神外资讯、神介资讯、神内资讯、脑医咨询、Ai Brain 所发表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脑医汇及主办方、原作者等相关权利人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