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单一分科治疗模式无法为胶质瘤患者提供全面且及时的诊疗,胶质瘤MDT则能根据患者疾病状况以及待解决的临床问题。MDT模式已成为肿瘤治疗的国际趋势以及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医疗团队诊疗和患者个体化方案保驾护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脑胶质瘤中心于2011年6月成立,是西部地区首家胶质瘤中心,也是国内唯一一个以脑深部肿瘤为亚专业的中心。2013年12月,在中心主任毛庆教授的倡导和组织下成立了脑胶质瘤MDT团队,融合神经外科、神经影像、神经病理、神经肿瘤、神经内科和康复科等相关学科,每月1次MDT讨论会,开设多学科联合门诊,编辑整理胶质瘤MDT病案荟萃,开展多项临床研究等,尤其在以丘脑胶质瘤为代表的深部肿瘤中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2022年,华西胶质瘤MDT团队将继续秉承“以患者为中心提供最佳医疗服务”的宗旨,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MDT团队的各项工作,加强与各胶质瘤中心的交流合作,促进我国胶质瘤事业的发展,将开展一系列远程院际交流,也会定期发布相关内容,供广大同仁一起学习交流探讨。


毛庆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神经外科
任中国医师协会脑胶质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3D打印技术分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脑胶质瘤专业委员会西南学组主任委员
四川省神经外科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脑胶质瘤协作组组长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微侵袭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委员
在国内外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了SCI及其它论文100余篇,先后承担省部级重点科研攻关项目10余项,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奖1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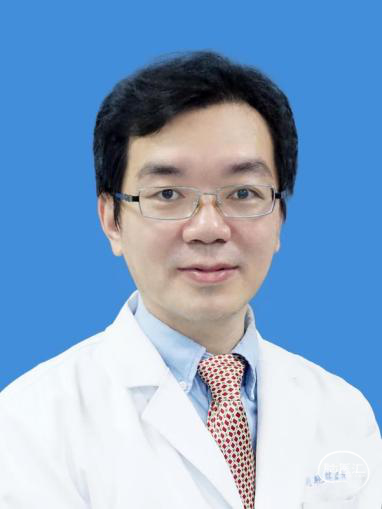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神经外科
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胶质瘤专委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显微神经外科专委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委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脑胶质瘤专业委员会西南学组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会神经医学分会常委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神经外科专委会常委
四川省肿瘤协会中枢神经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四川省卫健委学术技术带头人
四川省医学会神经外科专委会副主委
四川省医学会神经肿瘤学组副组长
成都市神经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万锋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神经肿瘤分会秘书长兼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脑胶质瘤专业委员会基础研究与转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小儿神经外科全国委员
中国胶质瘤协作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脑胶质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神经系统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儿童肿瘤精准诊疗协作组副组长
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胶质瘤专委会常委
国家自然科学金评委、教育部回国留学启动基金评委
Case1
病例分享讨论-华西-同济毛细胞星型细胞瘤各一例
![]()
王翔教授(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
讨论:1. 诊断鉴别 2. 下一步治疗方案。
![]()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万锋教授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万锋教授
![]()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两个病例确实非常有意义,从年龄、发病部位、疾病的进展、手术切除程度及治疗行为都非常相似,先请影像学老师从影像的角度谈谈诊断意见。
 华西医院影像科月强教授
华西医院影像科月强教授
谢谢两位影像科老师,综合两位老师意见来看,毛星的概率更大。回到病理诊断,先看看同济的病例病理诊断是否非常确切?请柯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 同济医院病理科柯昌庶教授
同济医院病理科柯昌庶教授
这个病例的光镜组织学特征还是符合毛细胞星形细胞瘤的诊断,第一,从组织结构分析到,部分肿瘤的组织疏松和致密双相排列,局部有黏液变性,低倍看瘤细胞有拉长的双极性的毛发样的胞浆凸起,第二,瘤组织内未见坏死,瘤细胞异型性不明显,Ki-67的标记指数3%,提示肿瘤细胞增生活性较低,所以根据肿瘤的组织学和免疫组化特征来看,支持毛细胞星形细胞瘤的诊断,当然最主要的还需要一个分子检测,如果证实有KIAA-1549和BRAF融合基因的异常,那就更为支持毛细胞星形细胞瘤的诊断。尽管分子检测阴性结果,不能够完全否定毛细吧星形细胞瘤的诊断。那么如何解释另外一个颅内病灶的发生呢,一个可能性是双重发病可能,第二个可能是小脑肿瘤的播散,就此请教一下万教授,这个小脑肿瘤是否累及到脑室的表面?
![]()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万锋教授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万锋教授
手术中的印象不是很清晰了,应该是在脑实质和四脑室没有关系,从解剖关系来看,并没有说从上蚓部和中脑背盖之间没有直接毗邻侵犯,推测是通过小脑上脚的纤维弥漫过去的。但是刚才我们华西影像科的老师也说了,病理上应该说毛星是局限型的,但毛星有个特点通过脑积液播散的现象,华西的病例好像又不是通过脑脊液的种植,同济医院这个病例就更不是脑脊液播散的。
![]() 华西医院病理科陈铌教授
华西医院病理科陈铌教授
同济的病例从病理的角度来看,形态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毛细胞星形细胞瘤。确实像刚才柯主任讲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图有一点粘液样的背景,细胞呈双极性表现,左边和右边显示的是不同的形态学区域,可以看到微血管增生。在看到微血管增生时,要想到毛星和胶母的鉴别,因为他们都可以出现微血管增生。如果看到微血管增生时,排除 WHO 4级肿瘤的可能性,就要去考虑1级的肿瘤,这是我们需要去鉴别的地方。这个病例从它的Ki67指数及其他一些表现,考虑毛星是没有问题的。该病人提供的分子检测应该是做的是泛生子的825基因panel,结果没有检出BRAF V600E突变。如果考虑毛星最重要的是检测有没有BRAF和KIAA1549基因的融合。这两个病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没有毛细胞星形细胞瘤的经典的 BRAF改变。毛星里面的大概75%存在BRAF基因分离,还有10%左右是BRAF基因突变,也就是说100个毛星里面可能有15个毛星不会检测到BRAF基因的改变。所以我个人考虑可能在我们诊断的毛星里面,可能可以分为这样两群,有BRAF基因改变和没有BRAF基因改变,这两组病例的生物学行为可能存在差异。当然我们之后也可以去总结一下这些病例,因为我们经典的毛星大部分的生物学行为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如果像这两个病例第一次没有完全切干净,特别像华西的病例好像一直都有残留,且有多次复发的过程,预后就不太好。所以毛星的生物学行为可能与它的切除程度和它的基因改变有一定的关系。对于同济的病例,我非常赞成毛细胞星形细胞瘤的诊断。华西的病例在今天讨论之前我只看到第四次手术的切片,不清楚病人有如此复杂的病史。因为这个病例最早2013年诊断的时候,应该是形态学和影像学都比较典型的毛星。我们复习的病例已经是患者2020年第三次复发的切片,已经没有那么典型。但这一次依然可以看到它有两种形态,左边的哪张图可以看到细胞呈巢团状结构,稍微有点粘液的背景,细胞有双极性改变;右边这张图上显示了一些罗森特纤维,其实切片上还有很典型的这种区域。从这种双极性的形态学表现,加上影像学,我个人觉得该病例还诊断毛星的可能性比二级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而且这个形态确实不太支持少突星形细胞瘤的形态,整体的形态学更符合毛星。但是最关键的就在于这个病例做了BRAF的突变检测,也做了BRAF的FISH检测,但是这两个改变都是阴性的,可能跟病人的生物学行为有一定的侵袭性有关系。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合理。总之个人觉得这形态学还是更支持是毛细胞星形细胞瘤,请教一下柯主任的意见。
![]() 同济医院病理科柯昌庶教授
同济医院病理科柯昌庶教授
同意华西医院陈铌老师的诊断,是一个毛细胞星形细胞瘤,因为它有一个双相结构,有疏松区和致密区,左边那个图可以看到黏液区域比较多见,我有一点推测:是否属于毛细胞星形细胞瘤亚型之一,毛黏液星形细胞瘤的可能。当然一般来说毛黏液星形细胞瘤是婴儿多发的,发病部位好发于下丘脑。虽然本例患者的年龄和发生部位并不典型,只是组织形态学上提供一点线索,是否毛黏液星形细胞瘤会出现较多的黏液性成分。请教一下陈老师,本例组织切片中黏液背景成分在肿瘤组织里占比成分多吗?同时根据患者多次肿瘤手术的病史,术后的病理改变也可能会影响肿瘤组织的病理学特征。
![]() 华西医院病理科陈铌教授
华西医院病理科陈铌教授
第一,这个病人最初发病年龄为5岁,毛粘液样星形细胞瘤一般两岁以下较多;第二,他的初发部位是小脑蚓部而不是下丘脑,所以说整个年龄和部位都不是典型的毛粘星表现;第三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是第三次复发的组织形态了,切片里依然可以看到两种形态,切片中两种形态的比例是1:1。
![]()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谢谢以上两位病理专家的分析,应该说这两个病例的病理诊断还是比较明确的。今天两个病例的特点是没有检测到典型的BRAF V600E的改变,病人最后的预后不如大家期待的常规的毛星那么好。除了刚才大家谈到的发病部位,手术的切除程度不是特别完美以外,应该和病理特点、分子特征也存在一定关系,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索,整理以前类似病例,观察V600E有突变的和没有突变的预后情况。再看治疗,两个病例都是小孩,手术未全切,因为家属各种考虑,再加上病变所在的部位,存在对放疗的顾虑,没有做常规放化疗,两个病人都在相对不长的时间内有所进展,所以后续治疗是不是可以更积极或者是更主动一些,请肿瘤科老师谈谈建议。
![]() 华西医院肿瘤科吴昕教授
华西医院肿瘤科吴昕教授
对于放疗,确实放射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比较慎重的。像毛细胞星形细胞瘤这种低度恶性的肿瘤,如果第一次切彻底了,那么一般是不做放疗的。当然如果是术后有复发,那么放疗还是可以介入的。华西这一例病例,做了4次伽马刀,伽马刀的疗效还是比较好的。第一次,脑干里面没有切除干净病灶,做了两次伽马刀以后,控制了一年多的时间。第二次,就是2015年和2017年,外院术后没有切干净的肿瘤,伽马刀也达到了局部地控制了肿瘤。所以,这个病人的肿瘤细胞应该是对放射线有一定敏感性的。我个人认为,当是病变范围较广,辅助调强放射治疗可能会有更好地效果。如果该患者没有办法再做手术,我考虑内科治疗方法有三个:一个就是化疗,一个靶向治疗,然后放射治疗。化疗有文献报道伊利替康加上贝伐珠单抗,贝伐珠单抗10mg/m²,伊利替康两周一次。30多例低级别胶质瘤患者,结果显示半年PFS有80%,两年PFS有30%,所以是可以先尝试的一个方案;因为BRAF没有突变就没办法尝试D+T的靶向治疗。如果内科治疗能够让肿瘤缩小控制,能够为我们放疗争取更长的间隔时间,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如果后续肿瘤进展,我觉得放疗还是可以考虑的。他现在是14岁,放疗对这个年龄没有问题的,我们主要的顾虑是在于他之前做得多次伽马刀的剂量。我们会收集之前伽马刀的剂量图和DVH图,然后对比伽马刀的部位是不是手术已经切掉了,如果切掉了,影响会减少。如果没有切掉,比如说脑干里面是手术没有切掉的,那么对于这个地方的剂量,我们可以做一个折算。毛细胞星型细胞瘤的放疗剂量是5400左右,之前如果照射了一个剂量,根据时间间隔,我们折算它的30%-60%,可以给勾画出来做一个降量保护,其它地方正常放疗,可能会对肿瘤控制有一定的帮助。
 华西医院肿瘤科艾平教授
华西医院肿瘤科艾平教授
针对华西的病例我也比较同意吴昕教授的意见,因为做过4次伽马刀治疗,其实最关注的就是丘脑和脑干的受量的问题。那么下一步针对外科切除以后残留的病灶,判断能不能够再做放疗,最关键的是要把四次伽马刀的剂量分布图恢复一下,看看脑干和丘脑的受量有多少,因为复发病灶都是毗邻脑干和丘脑的,所以说最关键的是依据对脑干和丘脑的损伤风险问题评估来判断有没有再次放疗的机会。另外,内科治疗当然是可以考虑尝试的,该病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棘手。对于同济的病例,是可以考虑放疗的。因为从来没有做过立体定向放疗或普放,10岁了,在低级别的胶质瘤明显残留的这种情况下,放疗是可以大胆做的。在放疗的同时,是否联合化疗,因为它是1级,化疗可以暂缓一下,就是说先单纯做放疗,这是我的意见。
![]()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万锋教授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万锋教授
提出两个问题,如果这次做放疗的话,中脑被盖的顶盖区的三年没有任何进展的这一块,在靶区勾画时需要包进去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从我们神经外科的角度来说,这一次小脑蚓部的复发病灶,再次手术可以把它切得非常干净,同时基于中脑被盖的病变,三年没有任何进展,是不是可以术后继续观察、不作任何处理?两个方案今天想特别提出来请教一下华西的老师。
 华西医院肿瘤科艾平教授
华西医院肿瘤科艾平教授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之一是,首先中脑被盖地方的病变肯定不考虑手术切除的,那么现在它就是两个病变,中脑被盖和小脑蚓部病变。刚刚影像学的老师讨论了,都认为中脑被盖病变是肿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一点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两个病灶相隔不是特别远,做放疗就建议一起做。暂时不考虑把小脑蚓部病变做手术,中脑病变做放疗的方式。做了放疗以后,根据随访疗效,如果小脑蚓部病变效果不好,再考虑行挽救手术。
![]()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对“小脑蚓部进行手术切除,中脑被盖随访观察”方案是一个选择。因为两个病变可能是一个病变的两个不同部分,有部分是强化,有部分是没强化,从第一张片子轴位来看是连续的,从小脑蚓部到松果体区,然后逐渐蔓延到中脑的被盖,强化部分在较低的位置,中脑区域没有强化的病变,可考虑做个弥散成像,了解是否有弥散受限。这几年影像无明显进展,也无症状,所以同意中脑被盖暂时观察。至于小脑蚓部这块是不是进行切除,这就是回到了手术切除程度的问题,包括上期也跟西安的老师进行了讨论,“相对生长缓慢的肿瘤,大家切除程度要求是否可以不那么高;肿瘤进展慢,担心功能障碍是否就切除可以稍微保守一点?”。其实刚才毛庆教授也提到:外科应该有所担当,手术切除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因此一定要尽可能切除彻底,为预后创造更好的条件,否则在实体瘤存在的背景下,后续治疗方案如伽马刀、放疗、内科治疗、靶向等,无论是从治疗周期,治疗费用,还是治疗的副反应都会比较大,所以第一次手术尽可能的切除彻底。二次手术需要综合考虑,首先就是病变进展程度,如果一直稳定在一个较小的体积,就不一定非要再做手术。再次开颅可能会在精神上、心理上、功能上的创伤以及治疗花费各方面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因此我们做二次手术还要综合患者意愿、家庭生活方面等进行综合评估。所以“小脑蚓部进行手术切除,中脑被盖随访观察”方案是一个选择,但手术不一定非做不可,实际上看起来这2年没有做任何干预的情况下,伽马刀、放疗都没做的情况下稍微进展零点几到一厘米,至少外科手段不是那么迫切。当然必须保持严格的影像随访,如病变有发展的趋势,应及时再次手术。
![]()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王翔教授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王翔教授
事实上手术除了切除难度以外,还在于术中的识别,包括同济的病例,小脑蚓部不好识别,中脑被盖也不易识别到,所以还在于这个问题,识别不到的话就很容易下来造成功能废除。我自己通过这两个病例也有体会,实际上对于较低级别的,原来我们会认为容易全切、预后可以、不会进展,事实上切除完全的病人术后预后很好,但也有未全切的病人术后也很好。所以对于类似低级别的胶质瘤,我们需要病理科的帮助去认识它,然后帮我们识别到底真的是一个低级级别的、还是很稳定惰性很强的、还是真的有可能复发机会的。同济病例如果在早期做放疗,能够识别早做放疗可能会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包括华西的病例当时除了做伽马刀以外,早期的放疗范围大一点,可能也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万锋教授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万锋教授
非常同意刘师兄的几个观点,第一个就是这种低级别的,特别像局限型的,咱们神经外科医生还是尽量切干净。因为部分残留的这类肿瘤,还是会有进展和复发的。所以即使这种低级别的还是尽量把它全切,有可能达到治愈;像华西病例难度本身就不可能全切,全切之后肯定下来就有神经功能障碍,但是像同济病例手术相对简单,难在最后的清扫,需要一点都不留、需要仔细和耐心。如果有术中磁共振可以帮助我们。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示我们,像这种低级别胶质瘤,某种程度上来说把它全切、清扫干净可能意义更大。然后这两个病例不知道我们这边的肿瘤科的老师有没有什么分享和讨论的意见,可以说一下。
![]() 同济医院肿瘤科席青松教授
同济医院肿瘤科席青松教授
我们这边说一下这两个病例后面的治疗,对于这种极低级别的这种儿童胶质瘤的话,患者手术之后可能很多都是可以长期生存的,所以放疗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延迟介入,或者是尽量推迟介入。因为做了放疗,可能会影响这些患者的一个长期生存的大脑功能,同时如果后期患者需要再次手术的话,也增加了手术困难,所以说对于术后有残留,也可以采取观察的策略,同济的病例病灶比较小,患者没有什么症状,放疗也不是必须要现在介入,至于手术的需求也不迫切,个人认为密切观察比较好。华西分享的这个病例患者存活了大概9年时间,反复做了5次手术和4次伽马刀,现在的情况是多个病灶的复发,再次手术并不合适。再次考虑放疗的话可能风险比较高,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们在临床上不会考虑给这种病人再次做放疗,可能会采取全身化疗,另外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可能通过脑室内植入一个Ommaya囊(欧玛亚囊)做鞘内的化疗,这可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但是没有看到有相关的报道,不知道这种策略会不会合适点,这样使这个患者全身的毒副反应更轻一点,同时局部血药浓度浓度会更高,会不会效果更好?我想问一下华西是否有相关经验。
![]()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王翔教授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王翔教授
华西上锦做过几次脑转移的肿瘤,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类似的患者的话,觉得很难可以送过来可以做,因为他们主要是两个目的,第一,放脑积液降低脑压,因为脑膜转移的患者确实后期很痛,第二,可以打药进去,这两个完了可以穿3000次左右,可以穿刺,可以抽血抽液。
![]()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以上两个病例非常有意义,一直以来临床外科医生认为毛星因为相对局限、生长比较缓慢,绝大多数手术能够全切,预后都比较好;即使有些没有全切,对于有BRAF V600E突变的患者,也有靶向药可以选择,但今天这两个病例相对预后不是那么好的,对于病灶在后颅窝往幕上延伸,也对诊疗提出了挑战。以后这类复杂的困难的病例可能还越来越多,非常需要大家进行多学科的、多院际的交流,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都对毛星的认识更深刻,下次遇到类似的病变,外科首先想到尽可能切除彻底,病理分子分析做得更细致更全面,术后酌情适宜的选择伽马刀或者普通放疗。
case2
![]() 王志豪老师(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王志豪老师(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 左右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
![]()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简单进行补充,该病例是比较典型的高级别胶质瘤,我们反复提倡规范化诊疗,我认为规范化需要每个环节都规范。术前影像发现病变,如果能评估术前代谢影像包括一些灌注等信息可能更好,术前评估包括认知功能也可以做得更全面。治疗方面采用了标准的同步放化疗加辅助化疗,后面又运用了国内开发的电场治疗的临床试验,所以我们按照临床试验来走,后期的影像检查就比较细一点。我们对临床研究病人可能投入的心血、时间、关心更多,治疗环节跟进的更细,信息收集的也更全,我们平时诊治的每一个病人都应该按照gcp来认真做好每一个诊疗环节和资料收集。接下来请教各位专家电场的使用时间的考量:一般电场有两个使用时间,一个是放疗同步结束以后辅助时间使用,一个是在开始放疗期间就使用。华西的这个患者3月份开始做辅助,2月份放疗完后就开始使用电场。对电场使用的时间请教下同济老师们的临床方面经验,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华西医院影像科月强教授
华西医院影像科月强教授
华西病例应该说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胶质母细胞瘤的表现,同济的病例在治疗期间复查的时候,发现原发病灶的部分有一个新的强化灶,这个在胶质母细胞瘤里面比较常见的,因为它比较靠近原发灶,所以从原发灶外延可能性比较大。我看到武汉的同时也是在画的GDP的范围之内采用相同的一个治疗,效果也还是比较好,但从长远看,那个地方可能会是最终复发的根源。
![]() 同济影像科张佳璇教授
同济影像科张佳璇教授
华西医院分享的这个病例,诊断是比较明确的,病灶的强化方式,是比较典型的胶质母细胞瘤的表现。同济医院这边分享的病例中右侧额叶较大的病灶也是比较符合高级别胶质瘤的影像表现,但同时右侧颞叶和左侧额叶还有两个小病灶,这两个小病灶完全没有强化,符合低级别胶质瘤的表现,当时考虑的诊断是多中心胶质瘤。右侧颞叶病灶大概1cm左右,左侧额叶病灶更小,这两个病灶随访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变化,当时手术完全切除了右侧额叶的病灶,但很快在切除病灶的后方侧脑室右侧出现了病灶播散,这也比较符合高级别胶质瘤的特点,这个病灶在放疗以后,中心坏死增多,明显好转,他目前右侧额叶的病灶是呈术后改变,没有复发的征象,其它部分没有明显变化。
![]() 华西医院病理科陈铌教授
华西医院病理科陈铌教授
这两个病例诊断都是没有问题,华西病例是胶质母细胞瘤,IDH野生型,TERT突变,属于预后最差的亚类。同济的病例这种情况,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遇到的情况,临床研究生收标本收得太多,留给病理医生的太少。这里特别感谢华西脑外科的老师,送的标本都很有代表性,从来没有出现活检高级别,手术切除低级别这种情况。
![]() 同济医院病理科柯昌庶教授
同济医院病理科柯昌庶教授
同济医院这个例子实际上看来第一次的活检取材较成功,取到了有代表性的高级别胶质瘤成分,第二次切除的肿瘤组织,估计送检到病理科的标本不完整,最有可能是取自病灶边缘的肿瘤组织,边缘组织实际镜下看到的大部分是邻近的脑组织,其内见异型性明显的胶质瘤细胞浸润生长,我们复阅了第二次的切片,发现虽然没有微血管的增生,没有坏死,但仍可看到些小灶热点区域的细胞增值指数比较高的,同时可见到瘤巨细胞的出现,反映了高级别肿瘤在邻近脑组织内的浸润生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高级别的胶质母细胞瘤,其肿瘤组织的异质性是常见的特征,因此,必须保证所取材标本具有完全的代表性,这是正确诊断和分级的基础。我个人也有一些经验,有的时候在同一例胶质母细胞瘤的不同切片里,某张切片细胞很密集,但Ki-67只有5%左右,而另外一个切片,瘤细胞增生活性可以到30%。我们建议,如果对病变的诊断有怀疑的时候,不妨可以全面取材,可以多选择几个切片,重复一下相关的免疫组化标记,可能会便于我们更全面的更完整的认识到肿瘤的生物学行为。最后,我们对华西医院的例子,胶质母细胞瘤的诊断完全同意,除了组织病理特征,而且还有分子检测的指标,TERT突变的出现。
 华西医院肿瘤科艾平教授
华西医院肿瘤科艾平教授
国际上对于胶母的靶区勾画不像低级别胶质瘤那么一致,大家各有各的意见,当然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是EORTC和RTOG的勾画方式,它扩边是外扩两公分。对亚临床病灶扩边的研究数据,无论是从尸检的报告还是复发病灶距原来肿瘤瘤床周围的直径,一般是在两公分左右,2-2.5公分,80%以上的复发区域是在两公分以内,所以按照这个数据,我们中心是以两公分来外扩胶母的亚临床病灶。刚刚同济的老师也讲了,他做这个靶区勾画的主要考虑还是后一次的手术切出来二级的成分比较多,所以他外扩的是1.5公分,同济老师有他自己的考虑。但对于胶母来说,我们中心还是扩边至少2公分。
 华西医院肿瘤科姚兵教授
华西医院肿瘤科姚兵教授
我们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病例CTV在术后瘤腔外扩2cm左右,在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保证肿瘤照射剂量60Gy。如果周围有重要的结构,如肿瘤临近脑干、视神经,视交叉等,局部可给予50-54Gy。在勾画靶区时,经常要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定位核磁看到还有病灶周围异常的强化病灶,到底是手术的残留还是术后的改变?这个也是今天讨论的两个病例遇到的问题,需要术后的72小时以内的核磁共振检查来判断是否术后残留,对于后续的治疗有帮助。
 同济医院肿瘤科杨琳教授
同济医院肿瘤科杨琳教授
首先华西的老师分享的这个是非常好非常规范的关于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的病例,手术包括术后放疗的靶区、剂量都很标准,目前同步放化疗之后辅助电场治疗也是一个标准的治疗。
![]()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刘艳辉教授
以上两个病例,第1,关于电场使用时机,同济在放疗同步期间,华西是在放疗结束以后。关于放疗和电场的使用时间,最早我们参考JAMA EF-14的试验在辅助期间使用,所以包括最早到香港去治疗的病人,后来内地上市的产品,以及近一两年国内自主研发的国产电场治疗,大多数还是参照EF-14,按照放疗完以后再开始使用的。但近几年也陆陆续续有小样本研究报道把放疗和电场同时做,所以同济在这方面的尝试,我觉得确实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华西也有几个病例是在放疗的同时电场治疗,至少目前没有看见放疗和电场叠加的副反应,所以这块我觉得可以累计病例再观察,希望能够更早的起作用、更好的发挥效益,对患者的预后更好。第2,对同济病案提出一点建议,个人倾向第一次就进行手术。这个患者病灶在右额,是一个混杂的强化病变,中间有一个低信号的类似坏死的区域,周围水肿比较厉害,不管是胶质瘤还是转移瘤,再发展下去,无论是对肌力、对癫痫、对颅压、对认知,都会有一个不利的影响,如果直接做开颅手术行最大范围的安全切除,一是可以防止病变继续恶化,二是有效的改善症状,因此我倾向于第一次就积极开颅手术,以目前的外科技术、策略理念、辅助手段,对于右额的病变,相信同济的老师可做到非常好的切除。而且做两次手术也可能给病人也带来更高的感染风险和经济代价等。
case3
![]() 汇报人:陈梓荣老师(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汇报人:陈梓荣老师(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左右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这个病例我也请教过我们肿瘤科的几位老师,包括席教授龙教授,它的特点就是单一的额底一个巨大的复发的病灶,其他部位没有。它的转录组基因组有它的一些特点,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临床上讨论的是什么呢?因为髓母一般不复发,好的亚型的10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80%,但是一旦有复发的成活率不到5%。那么对于这一种特殊类型的复发,我们何教授当时那篇文章总结了文献的报告是20多例,那么对于这种特殊类型的复发,我也请教了咱们肿瘤科,三维视行放疗,为了保护视力是额底腮板的剂量是比较低的,但是也因人而异,说到底你多少都关注了这个地方,剂量给的是多少,能不能我们尽量的避免复发,特别是我们第一个病例很有意思,当时在三脑室底还有病变,经过综合治疗之后就消失了,最后就是单独的额底一个复发,最后一旦复发了,后面就反复复发,最后去世了。所以今天主要我想请教是对于咱们髓母的预防性的额底的放疗,有哪些细节是可以改进的,或者是因个体化的差异来尽量避免这种这种形势的复发。
 华西医院肿瘤科姚兵教授
华西医院肿瘤科姚兵教授
同济老师分享的三例病例很典型,髓母细胞瘤在完成手术治疗、术后放疗及化疗后,最常见的失败部位除后颅窝原发灶外,前颅窝底(筛板区)是最常见的部位,主要原因是前颅窝底的位置低,又与眼睛晶体临近,通常是由于全脑照射野的下界不够造成,所以在设计照射野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因为前颅窝未包全,靶区遗漏造成复发。我们在放疗计划制定过程中,重点关注前颅窝底(筛板区)部位的剂量,如果眼睛晶体剂量限量影响该靶区剂量提升,我们可以适当提高眼睛晶体剂量,如眼睛晶体提高到1200cGy;如果提高眼睛晶体剂量也无法解决,可以局部单独使用电子线小野补量,保证前颅窝底(筛板区)部位的剂量达标。筛板区部位和相邻野交界处的剂量是我们在做髓母细胞瘤全脑全脊髓放疗计划时重点关注的地方。
![]()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万锋教授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万锋教授
问一个问题,我们筛板的剂量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 同济医院肿瘤科龙国贤教授
同济医院肿瘤科龙国贤教授
这个地方是一个治疗难点,比较容易复发。剂量方面,我们也是全脑全脊髓给到3600cGy左右,再局部加量。但是现在也有一些进展,低危或者中危髓母细胞瘤,采取多药化疗联合放疗的治疗方式,主要是长春新碱、铂类、环磷酰胺等,也有应用替莫唑胺的。全脑全脊髓减量放疗,可以降到2600-3060cGy,再局部推量。计划设计方面,晶体PRV有时会给到1200cGy,超过900cGy,因为我们考虑肿瘤复发的风险太大,我们也会和患者沟通,为了肿瘤更好控制,争取靶区剂量覆盖完整,晶体适当牺牲超量。
总结
今晚华西和同济两个MDT团队在一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学习,探讨了两对胶质瘤(包括一对毛星和一对胶母)、两例髓母的放疗靶区的勾划,干货众多,时间紧凑,节奏较快,信息量大。往往一个中心的标准或者方案会相对局限,因此需要大家多互动多交流,才能相互取长补短,既开阔大家的眼界,也提升认识水平,更好的对临床工作进行指导,希望以后能够合作做一些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促进胶质瘤诊疗事业的发展!
会议预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胶质瘤多学科诊疗(MDT)院际交流2022年第4期
会议日期:2022年6月6日晚19:00-2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