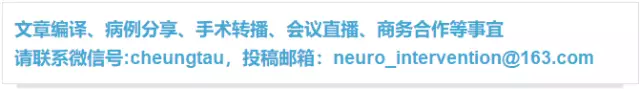

由周良辅、 孙颖浩院士作序,上海长海医院脑卒中中心兼神经介入中心主任刘建民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western医院Timo Krings教授任主编,黄清海教授、赵文元教授、洪波教授、许奕教授任副主编的《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基于病例的研究》精华版即日起于神经介入资讯连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本书的第四章: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常用技术精彩部分,欢迎阅读、分享!
本书的实体书也在神经介入资讯微商城发售(纸质书已全部发货,请您注意查收),长按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进入购买页面,精彩内容抢先观看!

长按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质图书
往期回顾
第四章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常用技术
一、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基本术式
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技术根据是否保留载瘤动脉可以分为重建性治疗和非重建性治疗两大类,以重建性治疗为主。非重建性治疗主要包括动脉瘤体及载瘤动脉的原位闭塞术( Trapping)和近端载瘤动脉闭塞术(Proximal occlusion)。应用此类技术后血流代偿性增加的部位发生新生动脉瘤的风险增加,多见于前交通动脉和基底动脉顶端,对于预期生存时间较长的年轻患者风险更高,发生率为7.3%一19.4%[1]。此外,并非所有患者均能耐受载瘤动脉闭塞,对于闭塞载瘤动脉后可能引起严重功能障碍者,术前必须行球囊闭塞试验。但即使术前球囊闭塞试验阴性,仍有4%~15%的缺血事件发生率[2]。因此,非重建性治疗目前仅作为部分难治性动脉瘤,如假性动脉瘤、末梢动脉瘤和夹层动脉瘤的可选方法。
重建性治疗技术包括单纯弹簧圈瘤内栓塞、球囊辅助栓塞、支架辅助栓塞和血流导向装置等方法,其治疗目的在于保持载瘤动脉通畅的同时,改变瘤内的血流动力学直至动脉瘤与循环系统完全隔离,以消除出血风险。其中单纯弹簧圈栓塞是最主要的方法,也是目前颅内窄颈动脉瘤的首选治疗方法。颅内宽颈动脉瘤早期被认为不适于采用介入治疗,多采用开颅夹闭治疗。但随着神经介入医师经验的积累以及新型介入材料的出现,颅内宽颈动脉瘤的介入治疗可通过采用微导管(丝)辅助技术、多微导管技术、球囊辅助技术和支架辅助技术及血流导向装置等实现。这几种方法互为补充,其中球囊辅助技术和支架辅助技术应用较多。
二、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入路的选择
良好入路是手术成功的关键,而合理的动脉入路选择也是动脉瘤血管内介入治疗成败的重要因素。现有导管鞘及导引导管的研发,使得超过90%以上的颅内动脉瘤能够通过经股动脉入路顺利完成。对于部分腹主动脉及降主动脉极度迁曲或扭转的患者,可使用长鞘以提高输送系统的支撑力;但依然有极少部分主动脉弓扭转患者,由于无名动脉、锁骨下动脉明显成角,通过股动脉入路的超选非常困难;对于此类血管径路的后循环动脉瘤,可以考虑通过同侧的桡动脉入路。
导引导管在动脉瘤的血管内栓塞治疗中发挥着提供支撑和径路的作用。因此,术中要求导引导管尽可能接近或超过颅底(颈内动脉岩骨段和椎动脉V2水平),特别是对于前交通和远端动脉瘤。在III型主动脉弓或伴有腹主动脉及降主动脉迁曲扭转的患者,应考虑使用长鞘以提供足够的支撑力。对于颈部血管迁曲明显的病变,可使用头端柔软的导引导管,特别是使用同轴系统的导丝导管技术,以促使导管尽可能输送到达理想部位,并防止发生颈动脉血管损伤导致的夹层。
三、微导管塑形与超选
如何选择合理的工作角度,是开始颅内动脉瘤栓塞治疗的重要步骤。三维旋转血管造影的应用,使术者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动脉瘤及载瘤动脉的空间三维结构。在动脉瘤的栓塞治疗中,避免弹簧圈突入载瘤动脉至关重要。因此,术中工作角度应该选择动脉瘤瘤颈切线方向的投照角度,而非按照动脉瘤的最大径进行选择。在需要使用支架或球囊辅助栓塞时,还应该充分考虑是否能够清晰显示远端血管结构。对于部分特别宽颈(瘤颈累及载瘤动脉周径1/2以上者)动脉瘤,从切线位上可能难以判断弹簧圈是否突入载瘤动脉内,可选择与瘤颈部位载瘤动脉轴线一致的投照角度,即“轴线位”或“马鞍位”。
在确定好工作角度后,应该根据动脉瘤及其与载瘤动脉的解剖关系进行微导管的准确塑形。用于动脉瘤栓塞微导管主要作用是输送弹簧圈的通道,可根据微导管的特性(顺应性或支撑力、管径等)和术者的经验选择。对于Willis环以远的末梢病变,应该考虑选择顺应性较好的微导管;而对于需要复杂塑形的病变,可选择支撑力较好的微导管。预塑形微导管头端有45°或90°单弯导管,也有J、S或C形弯曲的复合导管,在合适的病例也可选择直头的微导管。载瘤动脉和动脉瘤的角度决定着选择何种形态的微导管。良好的塑形是成功栓塞动脉瘤的第一步,根据瘤体纵轴和载瘤动脉的夹角、动脉瘤长径和载瘤动脉的直径,可以确定微导管塑形角度及长度[3]。塑形理想的微导管甚至不需要微导丝的导引,直接进入到动脉瘤内1/2的位置,并在填塞动脉瘤时,微导管能紧靠载瘤动脉的对侧壁获得必要的张力,使头端自由地变化位置,且头端始终指向瘤体方向。
四、弹簧圈填塞与常用辅助技术
(一)动脉瘤囊填塞技术
在栓塞动脉瘤时,对于形态规则且直径>7mm的动脉瘤,首枚弹簧圈的选择应略大于动脉瘤的最大径以利于成“篮”;但对于微小或形态不规则的动脉瘤则选择等于或略小于瘤体最大径的弹簧圈。部分呈“腊肠状”动脉瘤可以采取分部填塞(piece-by-piece)的方法,根据动脉瘤的宽度选择合适弹簧圈,而非最大径。其后根据填塞过程中微导管的位置及输送阻力选择后续的弹簧圈直径和长度;在收尾时弹簧圈的选择应采取“软、小、短”的原则。对于破裂动脉瘤,尽可能选择水凝胶弹簧圈或纤毛弹簧圈以提高即刻栓塞密度。
在弹簧圈栓塞过程应注意尽量缓慢填塞,避免正对破裂点;适当调整微导管的张力,以改变弹簧圈的走向,利于弹簧圈的成“篮”和填塞。成“篮”时应该很好地覆盖瘤颈;栓塞时出现分隔现象,可选择复合圈以利于改变方向,或者微导丝重新超选;解脱最后1枚弹簧圈,可将弹簧圈推送杆适当推出微导管外,缓慢回撤微导管,避免将弹簧圈带出,必要时使用微导丝。
对于部分复杂宽颈动脉瘤,可以采用双导管技术进行栓塞治疗,即在动脉瘤腔内放置两个不同塑形角度的微导管系统,经两个微导管交替送入弹簧圈使两个弹簧圈在瘤内互相挤压支撑而稳定在瘤内,观察弹簧圈稳定后再分别解脱弹簧圈[4]。重复以上过程直至动脉瘤完全栓塞。该技术使术者有机会在动脉瘤内先后或同时操控2枚弹簧圈,使弹簧圈适应动脉瘤形状既分布均匀又能稳定成“篮”,适用于相对宽颈(瘤颈/体比<1)的颅内动脉瘤。该技术具有以下优点:交互编织的弹簧圈在动脉瘤腔内的稳定性强,不易突入载瘤动脉,提高了囊内弹簧圈稳定性;双微管技术受血管的影响较小,适用于载瘤动脉迁曲的动脉瘤栓塞。但也有一定风险,如术中应用2根微导管同时操作,因技术难度增加而使缺血性并发症的发生率也相应增加;仍有微弹簧圈脱出瘤体的风险,不适用于颈体比>1的动脉瘤。
(二)动脉瘤的辅助栓塞技术
颅内宽颈动脉瘤是血管内治疗的难题,为避免弹簧圈填塞过程中突入载瘤动脉,可在载瘤动脉内采取临时性或永久性的辅助栓塞策略。其中临时性辅助栓塞技术包括,微导丝或微导管辅助瘤颈成形技术以及球囊辅助栓塞技术。球囊辅助栓塞技术(remodelingtechnique)由法国Jacques Moret最早报道[5]。该技术采用不可脱的球囊在动脉瘤颈部的载瘤动脉临时充盈,通过预置于动脉瘤内的微导管填塞弹簧圈,在解脱每枚弹簧圈前均需要回抽球囊内造影剂,以观察弹簧圈是否稳定于动脉瘤内。该技术的应用使得颅内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适应证得到很大的拓展。所使用的球囊从非顺应性球囊逐渐过渡到高顺应性球囊;双腔球囊导管的出现,也使得球囊辅助技术中的一些技术难点得以克服。与其他辅助栓塞技术比较,球囊辅助技术的主要优点包括:①瘤颈重新塑形,成“篮”更稳定,栓塞更致密;②由于血管内不需要置入异物,围手术期可避免抗血小板聚集治疗;③并发出血时可以充盈球囊临时止血。但由于需要阻断血流,可能引起血栓栓塞并发症及加重脑组织肿胀。同时,由于缺乏对载瘤动脉的永久保护而无法适用于特别宽颈、梭形及夹层动脉瘤。相对于支架辅助技术,需要反复多次的循环操作使其更繁琐。同时由于球囊限制微导管头端活动,张力不能释放,增加出血风险。
微导丝或微导管辅助栓塞技术是由刘建民等于2001年提出的,是指根据血管成角及瘤颈宽窄塑形微导丝或微导管,并将其放置于跨瘤颈的载瘤动脉内,对瘤颈起到暂时性保护作用。此类技术往往应用于血管直径较细的病变或动脉瘤远近端载瘤动脉成角较大的相对宽颈动脉瘤,如大脑中动脉分叉部或前交通动脉动脉瘤[6]。
自1997年Higashida等[7]和2000年刘建民等[8]分别报道了国际和国内首例球扩冠脉支架结合弹簧圈栓塞颅内梭形动脉瘤后,颅内动脉瘤的治疗进入了崭新的时代。随后多种颅内专用支架进入临床,包括Neuroform支架、IEO支架、Solitaire支架、Enterprise支架和LVIS支架等。不同的支架设计和输送与释放技术,要求术者详细了解不同的器具。同时,支架植入策略也从早期提出的“微导管穿越支架(Mesh)”技术和“支架稳定微导管(Jailing)"技术,逐渐发展出许多新的技术,如刘建民等提出的“支架后释放”技术、“支架半释放技术”、“并列型Y型支架”技术、"Y型支架(Y-configuration)”技术、“倒Y型支架”技术、"X型支架”技术、“冰淇淋(Waffle cone)”技术、“单纯支架(stmt alone)”技术、“挽救性支架植入(Bailout stmt placement)”技术和“支架水平释放(horizontal stenting)”技术等[9]。支架后释放技术有别于以往提出的支架外栓塞技术(stmt-jailing technique),后者是指在支架输送到位,将微导管超选进入动脉瘤,在应用弹簧圈填塞动脉瘤前将支架释放。而支架后释放技术是指应用1个或多个弹簧圈在动脉瘤囊内部分或完全填塞后再释放支架,以期获得更好的瘤颈覆盖。作为一种治疗策略是为了使支架将弹簧圈压在弧形的瘤颈外,形成更为致密的瘤颈覆盖而达到血管重建的目的[10]。
支架在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中,除了发挥机械阻挡作用,防止弹簧圈突入并保证载瘤动脉通畅;还可以改变载瘤动脉和动脉瘤内的血流动力学特性,促进瘤内血栓形成;同时,支架可促进瘤颈的生物学修复,有助于载瘤血管的重建,降低动脉瘤复发的风险。特别是重叠多支架植入更加明显地改变血流动力学,而成为梭形及大型动脉瘤的重要治疗策略。但支架辅助技术需要应用抗血小板聚集药物,有可能导致待栓塞的动脉瘤破裂出血、干扰和延迟动脉瘤内的血栓形成、增加后续开颅手术的难度和风险,对于支架在破裂动脉瘤急性期治疗中的应用仍存在一定的争议[11]。
血流导向装置(flow diverter, FD)作为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治疗的重大突破,体现了从动脉瘤囊内填塞到载瘤血管重建的治疗理念转变,为复杂性动脉瘤的治疗带来了全新的思路。作为一种新型的血管内治疗器具,血流导向装置主要用于重建动脉瘤的载瘤动脉,其设计聚焦于将血流从动脉瘤内导向远端血管以促进动脉瘤内血栓形成。与传统的血管内治疗技术不同的是,FD作为血流导向和腔内血管重建作用的结合,为颅内动脉瘤提供更加符合生理条件的治疗手段,而这一因治疗理念和靶点的转变而产生的新器具更接近动脉瘤病变治疗的实质。目前,基于血管重建的FD有Pipeline, Silk, Surpass, Fred和Tubridge等,更有基于瘤腔内重建的扰流装置,如Web和Luna等装置。Pipeline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颅内动脉瘤治疗的唯一FD,其被批准用于22岁以上,颈内动脉从岩骨段至垂体上动脉段大型或巨大型宽颈动脉瘤的治疗[13]。与所有治疗器具研发与应用相同的是,FD的临床应用也存在适应证的选择与拓展的问题。FD从最初被应用于大型、巨大型或其他办法无法治疗的颈内动脉动脉瘤,逐渐拓展到多部位不同类型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甚至是部分中心的首选治疗方案。当然,FD治疗依然存在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抗血小板聚集治疗的最佳方案和给药时间,对于未能形成瘤内血栓的动脉瘤进一步治疗方案以及如何防止出血并发症等[14]。应用FD治疗颅内动脉瘤已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合理适应证的确定,FD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有望进一步提高。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我们应认识到,即便是相同的病变也应该遵循个体化原则确定最佳治疗方案,新技术的应用需要更多经验的积累以使其更趋安全有效。
(段国礼 黄清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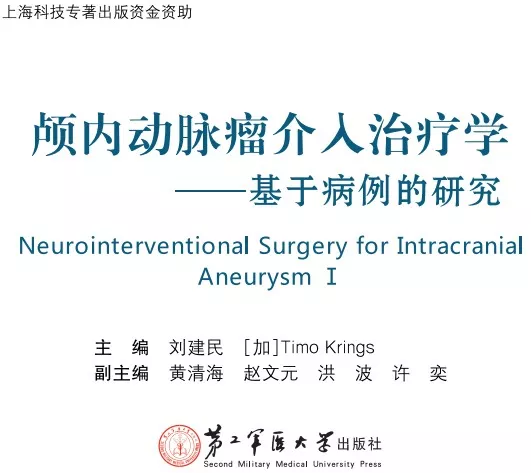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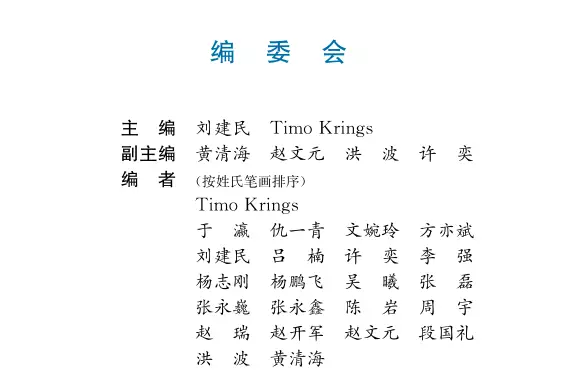
在先辈们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探索,神经血管解剖学、数字化影像学及介入材料学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革命性进步。随着这些新认识、新方法和新材料等快速完美的集成组合,使神经介入这一新兴的亚学科以令人惊奇的速度飞速发展,脑血管病的诊疗也进入了精准微创的新时代。这一新兴的技术已成为颅内动脉瘤、脑脊髓动静脉畸形(瘘)、头颈部供血动脉狭窄及急性缺血性卒中等脑血管病治疗的重要方法。尤其是随着神经介入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疗效的不断提高,治疗范围的不断拓展,颅内动脉瘤治疗的理念、策略和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患者因此获益。目前,国内外的指南已将介入治疗推荐为颅内动脉瘤首选的治疗方法。这一微创治疗新手段使颅内动脉瘤的治疗由巨创到微创、由难治到易治、变不可治为可治。作为医生,我们为拥有这种更安全、更有效、更微创的新技术去帮助患者远离疾病和残疾而兴奋不已。我也为能有幸成为一名神经介入医生深感自豪!
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虽然是一门微创治疗技术,但我们面对的是神圣的生命,其手术操作技巧最为精细且生死攸关。我们要付出多年的时间去学习与训练,使我们具备渊博的知识、灵巧的双手和训练有素的眼睛。在技术不断发展和迅速普及的情况下,有3点问题值得重视:(1)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强调个性化治疗,没有任何两个颅内动脉瘤完全一样,不同部位、不同病因及不同形态的动脉瘤所涉及的病理生理、自然病史、影像功能解剖以及手术策略和手术技巧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对术者的基础理论、手术决策和操作能力有较高的要求。(2)神经介入的手术效果与材料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材料学的更新换代极其迅速。因此,术者必须熟悉各种材料的特点和运用技巧,针对具体的病例,选择和运用最合适的材料。这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着手术的疗效和成败。这就要求术者具备大量的手术实践经验,同时,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和习惯,及时了解学科的最新发展,才能保证手术质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3)颅内动脉瘤的残死率极高,我们要设身处地的用最通俗的语言与患者和家属沟通,使他们了解自己疾病的真实情况并理解自己的病情,使他们能够做出符合自身情况的正确选择,并为今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成功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以生存或治愈,因为有大量的问题是目前医学科学技术尚无法解决的。最重要的是,无论病情多么复杂凶险,作为医者,都能竭尽全力,尽己所能。
1992年,在马廉亭教授组织的学习班上,我第一次接触到神经介入,便被深深吸引;1997年,在日本第一次看到GDC,更让我兴奋不已;1998年,参加牛津大学Byrne教授主办的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习班,我深深体会到神经介入的无穷魅力和面临的挑战。在学习、实践、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缺少经验,走了一些弯路,我开始思考如何持续学习,如何缩小国内外的差距,如何在我国推广并提高神经介入医生的同质化水平。为此,2001年,我们创办了OCIN,并手术直播了颅内支架成形术等10台手术;同年,开办了OCIN学院的第一期学习班;2003年,我们创办了每季度召开的以讨论并发症和死亡病例为核心内容的神经介入沙龙。如今,OCIN已成为神经介入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OCIN学院也将迎来第100期学习班;神经介入沙龙得到同行的广泛响应和认可,并逐渐在全国推广。2006年,我们创办了东亚神经介入论坛(EACoN),每年在中日韩轮流举办;2010年,我们顺利举办了世界颅内支架大会(ICS);今年,我们在上海又成功举办了世界神经介入治疗大会(WLNC)。以上的各个交流培训平台都是以病例直播和讨论为特色的。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临床医生从病例中学习提高是最快捷有效的方式之一,从病例中学习相关知识会更加生动并易于掌握。非常有幸,我在2011年的OCIN与Timo Krings教授相识,我们都非常热衷于神经介入治疗的培训和教育,在讨论这一话题时,我们的许多观点完全一致,并决定共同撰写一本基于病例研究的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经过多次的讨论确定了编写大纲,并精心挑选了长海脑血管病中心具有代表性的病例,反复商榷每个病例的特点和教学点,从病史、体征、影像、解剖、技术、材料、策略、并发症、围手术期处理、随访、存在问题及相关进展等方面详细解析,将我们二十多年的探索和积累的经验真实地融入其中,力求使读者在阅读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希望能从每个病例中吸取到所需要的知识。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想首先感谢国内外的前辈和同仁以及我的医疗团队,感谢你们无畏的探索、经年累月的默默工作和无私的分享,本书从你们艰辛的工作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同时,我要感谢我的患者和家属,医患同心,其利断金,你们的信任和坚持,给了我们实践的机会,解除你们的病痛是我们最大的前进动力。最后,还要感谢不断创新研发改进DSA设备及神经介入器械的所有科技人员及公司。他们不断创新的神经介入系列产品,使我们具备了更多的方法以更强的能力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刘建民
2016年9月于上海

刘建民 教授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全军脑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临床神经医学中心主任、神经外科主任、脑卒中中心兼神经介入中心主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秘书长兼出血性卒中介入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介入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神经系统疾病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介入医学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脑卒中分会主任委员,全军及上海市神经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医师定期考核介入医学专业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担任国内外10余本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副主编、编委或审稿专家。
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30余年,以脑血管病微创治疗为特色,开展颅内动脉瘤、脑供血动脉狭窄、急性脑梗死、脑(脊髓)动静脉畸形及动静脉瘘等脑血管病的治疗万余例,首创颅内支架侧孔成形术等11项新技术。
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及全军重大攻关课题等科研项目19项,主编专著2部,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发表论文526篇,其中SCI收录100余篇,主持制定脑血管病介入治疗规范及专家共识各1部。
创办东方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大会(OCIN)、东亚神经介入论坛、颈动脉狭窄论坛、颅内动脉瘤论坛,OCIN学院及神经介入沙龙,先后承办世界脑血管痉挛大会、世界颅内支架大会及世界神经介入直播大会。研发系列神经介入器具,目前已获得产品注册4项,完成临床验证并上报SFDA待批产品2项,正在进行临床验证产品2项。先后应邀在牛津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多伦多大学等7所大学讲学、手术演示以及在国际大会专题发言30余次。获教育部、军队及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5项。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育才银奖及“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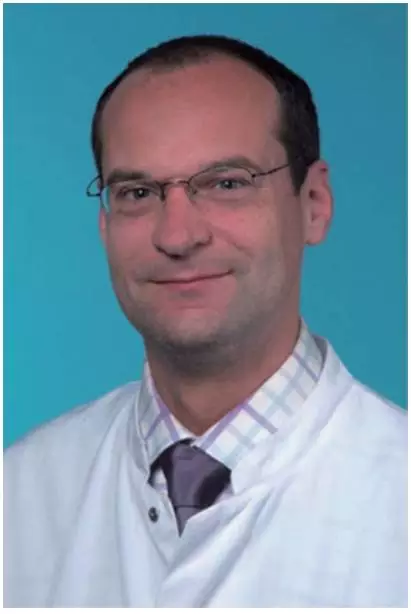
Timo Krings 教授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western医院教授、神经放射科主任、前欧洲神经放射协会副主席、欧洲神经放射学会科学委员会主席。Krings教授早年在德国亚琛医学院(Aachen)和美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学习,后长期与两任世界神经介入主席Rerre Lasjaunias和Karel ter Brugge教授合作共事,对脑脊髓血管的胚胎发育和影像解剖、脑脊髓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及其介入治疗积累了深厚的学养。
在亚琛医学院期间,Krings教授因神经系统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赢得广泛声誉,荣任德国最年轻医学教授,随后担任亚琛医学院神经介入主任。2008年,Krings教授赴多伦多大学工作,并接替了Karel ter Bmgge教授的职位。他先后发表论文170多篇,出版专著2部,参编30多本著作;兼任《Strake》《Brain》等26本神经领域相关高影响力学术期刊的审稿人,同时担任牛津大学、苏黎世大学、维也纳大学、东京大学等多所国际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其主编的《Case-Based Interventional Neuroradiology》通过具体的病例深入、系统地阐述了神经介入学相关疾病和理论,并对本书的编撰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国古代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年)说“无古无今”,英国莎士比亚说“What is past is prologue(凡往昔事,皆今序章)”,我们也常说“温故而知新”,可见古今中外都很重视历史。什么是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历史呢?这可追溯到20世纪初,由于颅内动脉瘤用银夹直接夹闭(Cushing, 1911年)不仅风险大,且疗效不好,因此外科医生尝试开颅暴露动脉瘤后,用银丝经动脉瘤壁插入动脉瘤内,再接直流电促进血栓形成,或插入经消毒的猪毛或马毛(Gallagher,1963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带球囊的微导管,Luesenhop(1964年)、Serbinenko 和Djindjian(1970年)先后用这些导管,通过颅外的血管经血管内治疗颅内动脉瘤,开启了经血管内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先河。但是,由于血管内介入材料和制造工艺以及人们认识的限制,经血管内治疗颅内动脉瘤发展缓慢。直到1991年,Guglielmi与工程技术人员合作,研发了电解可脱弹簧圈(GDC)治疗颅内动脉瘤。GDC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创举,生动地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对医学的影响,GDC的出现和应用不仅使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从血管外发展到血管内,而且掀开了经血管内的神经介入新篇章。如今,虽然动脉瘤夹技术得以不断完善,动脉瘤显微手术也逐渐成熟,但血管内介入仍发展成为颅内动脉瘤治疗的主要方法,而且也成为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科学技术和医学的飞速发展,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理念、方法和器械约每隔10年就会发生变化。因此,知识和技术的更新与普及是当今我国从事神经介入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面临的任务和挑战。长海医院刘建民教授及其团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基于病例的研究》一书。刘教授及其团队对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他们把长期工作积累的大量病例汇集成书,通过各类典型的病例,生动、直观和系统地介绍各种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相关技术和理论要点,目的是期望读者能够按图索骥,比较迅速地掌握相关知识,指导临床实践。书中的病例选择充分反映了作者匠心,既考虑了不同的颅内动脉瘤,如不同部位、大小、形态以及动脉瘤类型对相应介入技术的要求,又针对性地选择了相关病例,以介绍相关特殊技术、治疗策略、术中和术后注意事项以及新材料、新方法。全书图文并茂,清晰易懂,重点突出,是从事神经介入医师和研究人员难得的一本案头参考书。
在此,我谨向本书的作者致以诚挚祝贺,并期待广大的读者开卷有益,从本书中汲取更多的知识,最终造福广大患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良辅
2016年9月
科技创新驱动医学的发展,转化医学成为近年的热门话题。所谓转化,就是用一个领域的创新指导衍生领域的突破。颅内动脉瘤诊疗在过去30年内有了重大突破,不仅从血流动力学等理论物理学角度分析血栓形成及动脉瘤愈合的机制,且栓塞材料也发生了从腔内致密填塞到血管重建的理念转变。而这些都得益于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成功转化,更是“产、学、研、医”合作的重大突破。正是神经影像技术不断发展以及神经介入治疗器具的不断更新,成为促进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领域飞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在学科带头人刘建民教授的带领下,从出血性脑血管病的栓塞治疗及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流再通等微创治疗技术应用,到脑血管病救治流程的改进、急救绿色通道的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和跨越式发展,已然成长为中国脑血管疾病微创治疗的一面旗帜。特别是在颅内动脉瘤微创治疗技术方面的创新性工作,更是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就,从开展亚洲首例颅内支架成形术治疗颅内动脉瘤,到支架半释放、后释放技术等一系列创新技术体系的建立,直至研发成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国产血流导向装置。作为刘建民教授的挚友,我有幸见证了该团队在这一领域坚持以“理论创新”指导“器具创新”,最终促进“模式创新”的全过程。这其中的艰辛和付出,尽管不足为外人道,但想必也已尽了“洪荒之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长海神经介入团队不仅执着于诊疗技术上的创新,更乐意于治疗理念与诊治经验的言传身教。《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基于病例的研究》一书正是该团队对神经介入教学从临床实践到理论的升华。本书是国内首部采用案例式教学模式的神经介入专著,精选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成功处充分体现了该团队的集体智慧,而失败处也凝聚了团队全体成员的深入反思与体会。每一篇章不仅有技术细节的展示,还着重讲解治疗方案制定及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更从疾病的解剖学及生理学特征进行介绍,充分发挥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的病例资源和学术资源优势。这不仅是神经介入初学者身旁的有用参考书,也是值得已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经验的从业者进一步学习提高的专业必备书。
在此,我谨向刘建民教授及其团队致以诚挚的祝贺,并期待他们以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为起点,从初始的病例积累到深入临床研究的开展,包括前瞻性注册研究、自然病史与出血危险研究、以及治疗方法的优化选择等,充分发挥病例资源优势,建立多中心的研究平台,占领颅内动脉瘤研究的“制高点也期望他的团队继续开展新技术,探索及总结神经介入诊疗经验,形成覆盖所有神经介入领域不同病种的系列丛书,进一步推广和普及中国的神经介入治疗技术及先进理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颖浩
第二军医大学校长
2016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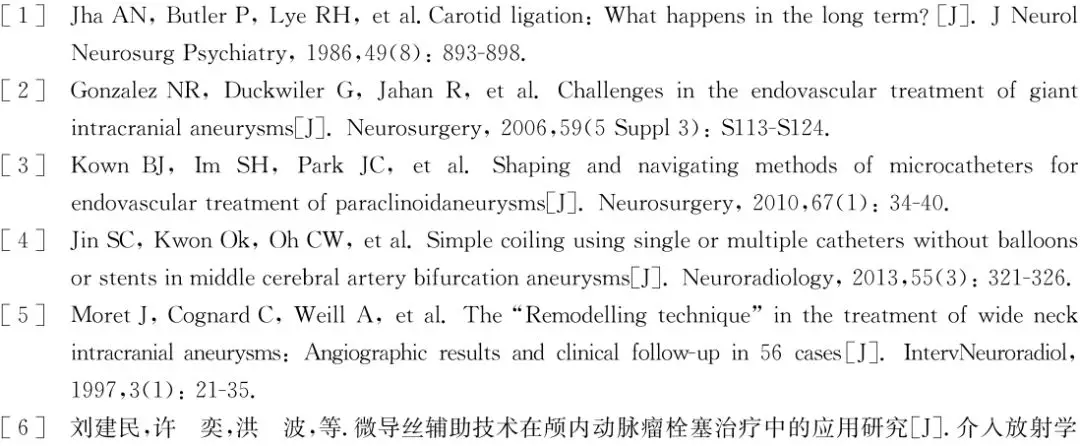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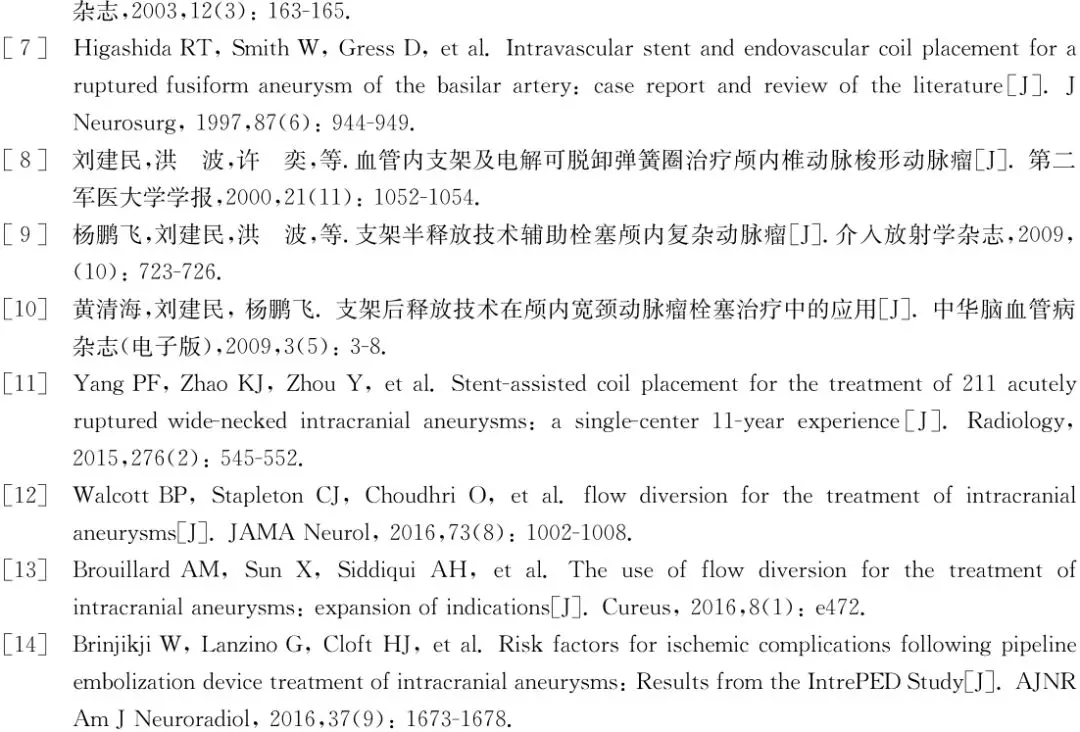
往期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