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谭启富癫痫外科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北京神经科学学会脑功能疾病与认知发育专业委员会,国家儿科及小儿外科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癫痫杂志》编辑部
执笔
张春青(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晓琴(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吴洵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季涛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郭燕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宋建平(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礼(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石先俊(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黄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张晓青(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通信作者:
张春青,Email:cqzhang@tmmu.edu.cn;
张建国,Email:zjguo73@126.com;
梁树立,Email:301_1sjwk@sina.cn
DOI:10.7507/2096-0247.2024030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071448)
脑皮质发育不良(Malformation of cortical dysplasia,MCD)是难治性癫痫的最重要结构性病因之一,占癫痫外科病理的19%[1],也是儿童癫痫外科最常见的病理,占比约40%[2]。外科手术是治疗MCD相关癫痫的重要手段,包括切除性手术、离断性手术、神经调控手术、毁损性手术等手术方式。预后分析显示MCD致痫区的完全切除是术后无癫痫发作的独立影响因素[3-5],而合理的癫痫外科手术技术是达到致痫区完全切除(含离断或毁损)的根本保障。因此,需要重视癫痫外科手术技术,以提高术后无发作率。
本共识主要就MCD相关癫痫,尤其是局灶性脑皮质发育不良(Focal cortical dysplasia,FCD)相关癫痫的切除性手术技术、下丘脑错构瘤(Hypothalamic hamartoma,HH)与脑室旁灰质异位(Periventricular nodular heterotopia,PNH)的立体脑电图(Stereoelectroencephalography,SEEG)技术及其引导的射频消融术(Radio frequency thermocoagulation,RFTC)技术、以及癫痫术后早期癫痫发作的防治形成专家共识。而涉及到半球、颞叶、岛叶和中央区癫痫的内容,此前已列入第三到第六篇专家共识之中,本部不再赘述。
临床问题1:不同MCD相关癫痫中难治性癫痫的比例一样吗?
推荐意见1:不同MCD相关癫痫的分子病理学机制不同,抗癫痫发作药物的选择各异,各自难治性癫痫的比例有所差别,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药物难治的(推荐比例96.8%,反对比例0.0%)。
少数FCD患者在初始治疗后甚至在癫痫确诊较长时间内可以实现癫痫无发作,但大多数患者药物治疗效果不佳[6]。HH所致的癫痫通常都是药物难治的[7],结节性硬化症(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TSC)患者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比例约为60%[8],PNH患者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比例大约为40%[9],皮质下带状灰质异位(Subcortical band heterotopias,SBH)患者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比例约65%[10],多小脑回畸形(Polymicrogyria,PMG)患者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比例约为65%[11]。
临床问题2:癫痫患者发现MCD,一定是致痫灶吗?
推荐意见2:MCD是癫痫的重要病因,但影像学发现MCD的患者不一定都伴随癫痫发作(推荐比例100%,反对比例0.0%)。
皮质发育畸形越重,伴发癫痫的可能性越大[12,13]。超过75%的MCD患者会发生癫痫发作[14],其中约49.5%的HH患者可出现癫痫及相关症状[15],几乎所有SBH患者均并发癫痫[10],80%~90%的PNH患者伴有癫痫发作[16],72%~85%的TSC患者有癫痫发作史[17],部分轻型半侧巨脑畸形(Hemimegalencephaly,HME)患者可无典型临床表现[18],超过90%的无脑回畸形患者伴随癫痫发作[19],78%~87%的PMG伴有癫痫发作[11]。
临床问题3:不同MCD的影像病理灶与致痫灶一致吗?
不同病理灶的病理学及组织学特征不同,各自的致痫性及其与致痫区的关系亦有所不同。大多数MCD病灶本身具有致痫性,病灶周围甚至远隔区域也可能是致痫灶。详述如下:
临床问题3-1:FCD的影像病理灶与致痫灶一致吗?
推荐意见3:多数FCD的影像病理灶与致痫灶一致,其致痫性及范围根据FCD亚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推荐比例96.8%,反对比例3.2%)。
在多数发育不良的脑回上都能记录到发作期或间歇期持续性的痫样放电,皮层脑电图监测提示FCDⅠ、Ⅱa、某些Ⅱb型本身具有致痫性[20],通过记录高频振荡活动也证实FCD的原位致痫性[21]。在磁共振反转恢复序列(FLAIR)呈“结节样”或“肿瘤样”高信号、内含气球样细胞的FCDⅡb亚型病变中,痫性活动分布有所不同,在富含气球样细胞的FCD区域(主要是磁共振序列上结节样改变的中心区域)致痫性最低,而皮质发育不良的周围皮质虽然不含或罕见气球样细胞,致痫性却更强[22]。值得注意的是,磁共振表现为阴性的FCDI型病例在临床上并不少见。高场强磁共振的应用将有助于FCD影像检出率的提高。
临床问题3-2:灰质异位的影像病理灶与致痫灶一致吗?
推荐意见4:GMH的致痫起源有单独异位结节起始、单独相关皮质起始及同时起始三种模式,且存在多个异位结节同时受累的情况(推荐比例96.8%,反对比例0.0%)。
脑灰质异位症(Gray matter heterotopia,GMH)的致痫灶有3种起源模式:癫痫发作在异位结节和功能连接的皮质(通常是上层皮质)中同时开始者占73.4%,在异位结节中起始发作为20.3%,只有很少情况(6.3%)仅由皮质起始[23]。癫痫发作时多个异位结节同时受累的情况并不少见[24]。
临床问题3-3:HH的影像病理灶与致痫灶一致吗?
推荐意见5:强迫性不自主发笑发作确认来自于HH,其他类型发作可能来自于HH内或HH外,甚至因为继发致痫性成为HH外独立起源(推荐比例100%,反对比例0.0%)。
1994年,颅内电极首次证实强迫性不自主发笑发作时的放电起源于HH病灶本身[25]。然而,部分患者的癫痫发作类型会出现变化,脑电图特征也会出现演变。颅内电极脑电监测发现,最初的致痫灶是依赖于原始病灶(HH病变本身)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继发性致痫灶可能会逐渐形成,并脱离原始病灶而成为完全独立的致痫灶[26,27]。这时即使切除原始的致痫灶,也不会影响继发性致痫灶的致痫性。
临床问题3-4:其它MCD的影像病理灶与致痫灶一致吗?
推荐意见6:PMG、结节性硬化、脑裂畸形的致痫灶较影像病理灶更为复杂(推荐比例100%,反对比例0.0%)。
尽管PMG具有内在致痫性,但致痫网络常常范围更广或发作起始区并不在影像PMG内[11]。结节性硬化的致痫网络还涉及到结节及结节周围组织,与影像结节并不完全一致[28,29]。脑裂畸形边缘的皮质、裂隙内的异位灰质都可参与致痫网络[30]。
临床问题4:对于FCD而言,全切除如何定义?
推荐意见7:全切程度的判断并非以FCD病变本身全切为标准,而是评估手术实际切除范围是否涵盖了术前预定的脑区结构(推荐比例96.8%,反对比例0.0%)。
FCD的切除范围由包括神经内科、影像科、神经外科在内的多学科小组在术前及术中确定,术后根据解剖学及电生理学数据仔细评估,以确定是否达到完全切除;只有当MRI结构异常区域和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放电异常区域被完全切除时,才被认定是FCD全切除[31]。
对于MRI阴性的FCD病变,即使通过详尽的多模态术前评估,也难以形成“标准的”全切除方案。此时,全切程度的判断并非以FCD病变本身全切为标准,而是评估手术实际切除范围是否涵盖了术前预定的脑区结构,即切除范围是否包含了广义上的癫痫起始区及临近的潜在(继发)起始区。MRI与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的融合影像、EEG特征性放电模式是勾画MRI阴性病例切除范围的重要手段。脑磁图、三维重建的高密度脑电图及具备后处理分析的高场强MRI等技术的应用,可提高FCD的全切率[32]。
临床问题5:FCD要达到术后无发作是否必须做到病变全切除?
推荐意见8:FCD病灶全切是术后良好疗效的最重要预测因素(推荐比例93.5%,反对比例0.0%)。
研究表明,FCD全切的患者中70%术后无癫痫发作,而FCD切除不全的患者只有22%实现无发作。因此,提高FCD手术全切率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尽管目前已常规开展长程视频EEG、高分辨率MRI、PET-CT和认知精神测评等标准的术前评估流程,但对FCDⅡb亚型之外的弥散性FCD病变范围的界定仍不理想,许多病例难以达到全切。此外,FCD病灶位于重要功能区或脑深部结构也是难以进行手术全切的重要原因[31]。对于范围较广、累及多个脑叶的FCD病变,可行脑叶离断手术;相较传统的切除性手术,脑叶离断术创伤小、癫痫网络破坏彻底,可达到“功能性全切”的疗效[33]。对于影像学上具有明确沟底征的FCD病例,近来的观点认为仅仅切除发育不良的脑沟即可达到与全切除相仿的癫痫控制率[34]。
临床问题6:通过哪些手段能够实现FCD的全切除?
推荐意见9:FCD全切除的概念至少包含两个层面,即在理论层面上正确界定切除的范围,以及在技术层面上实现目标区域的完整切除(推荐比例96.8%,反对比例0.0%)。
FCD切除范围的界定需要多学科协作来共同完成,术前评估资料包括症状学表现、EEG、MRI、PET-CT、脑磁图(MEG)、神经心理评估等。从神经影像学的角度来看,FCDⅡ型可出现特征性MRI改变,如皮质厚度增加、灰白质边界模糊、漏斗状穿透征等,这些特征使FCD的切除范围实现“可视化”。然而,21%~58%的FCD病变在传统MRI序列上无法识别,因此仍需更先进的成像技术不断应用于FCD的术前评估,包括高场强(7T)MRI、弥散张量成像(DTI)、弥散峰度成像(DKI)等。此外,MRI与PET-CT融合影像以及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可显著提高FCD的检出率[35]。EEG特征性放电亦是确定切除范围的重要参数,如FCD的头皮EEG可见与致痫灶部位相关的节律性癫痫样的放电(REDs),颅内脑电记录可见连续性癫痫样放电(CEDs)等。
对于功能区外的FCD患者,可基于术前评估的致痫灶以及术中脑电监测所提示的放电区域行裁剪式切除。对于FCD位于重要功能区的患者,可在术中唤醒和(或)皮质电刺激监测下行致痫灶切除术,此时需要在功能保留与FCD全切之间进行权衡。近年来,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术中磁共振、术中超声等技术的应用[36]可提高MRI阴性FCD及脑深部FCD的手术全切率。
临床问题7:HH患者的SEEG设计的要点有哪些?
推荐意见10:电极置入的策略与致痫区范围有关,其核心策略是使HH内尽可能多地分布电极触点,并确保电极触点覆盖瘤蒂周围,同时还应考虑是否存在下丘脑以外的致痫区(推荐比例96.8%,反对比例0.0%)。
SEEG电极置入的策略与癫痫发作类型及致痫区范围有关。对于有强迫性不自主发笑的癫痫发作,电极通常可直接放置在HH本身[37]。由于HH病变位置较深,电极置入路径较长,因此SEEG靶点及路径设计需规避脑内动静脉、第三脑室以及穹窿、乳头体等重要结构,并根据HH形态、体积、瘤蒂的分布特点设计电极的靶点和数量,其核心策略是使HH内尽可能多地分布电极触点,并确保电极触点覆盖瘤蒂周围。通过这种方式,可全面描记HH的放电模式,并有利于后期利用RFTC最大限度的毁损HH病变[38]。然而对于其他类型的癫痫发作,下丘脑以外也很可能存在有独立的致痫区[39]。在这种情况下,SEEG电极应尽可能靶向所有可能参与致痫网络的结构,例如扣带回边缘系统、额叶和颞叶皮质的中外侧[40],以精确定位致痫灶和指导后续的RFTC。
临床问题8:PNH患者行SEEG时其设计的要点有哪些?
推荐意见11:成功的PNH-SEEG方案是将电极置入假定的致痫结节、周围皮质和直接传播区域,单纯针对结节的置入方案需谨慎(推荐比例100%,反对比例0.0%)。
PNH最常见的放电模式是结节和外围皮质同时起源,此外灰质结节本身、结节外的远隔皮质甚至颞叶内侧结构亦可见痫性放电起源,因此癫痫症状学及头皮EEG结果仍是设计PNH电极置入方案的重要依据。成功的PNH-SEEG方案是将电极置入假定的致痫结节、周围皮质和直接传播区域,单纯针对结节的置入方案需谨慎。由于RFTC已成为PNH一线治疗方法,因此可考虑在推定的致癫痫区域进行密集置入[41]。
临床问题9:HH和PNH患者行RFTC时的操作要点有哪些?
推荐意见12:PNH的灰质结节有时会整合入功能性皮质网络,因此PNH的RFTC预毁损需引起重视;HH的瘤蒂是RFTC的重点靶区(推荐比例100%,反对比例0.0%)。
经SEEG引导的RFTC已成为HH和PNH相关癫痫的推荐治疗方法。RFTC毁损通常在清醒状态下进行,开始前需常规核对拟毁损电极触点的位置;随后进行预毁损,选择短时、低能参数(功率1~3W、时间30~50s),期间动态观察患者语言、运动等功能的变化,由于PNH的灰质结节有时会整合入功能性皮质网络,因此PNH的RFTC预毁损需引起重视。预毁损未出现神经功能缺损的患者,可增加功率(3~8W)和时间(30~60s)进行永久性毁损,同时不断观察患者语言、运动等功能。痫灶内距离较近(≤7mm)的电极触点,可进行不同电极之间3D交叉毁损。HH的瘤蒂是异常放电的传导通路,瘤蒂离断是控制发作的最有效途径,因此瘤蒂是RFTC的重点靶区。毁损后可继续进行SEEG脑电监测,观察毁损区域放电情况,根据结果直接拔除或再次热凝;RFTC结束后再次评估神经系统功能,并行影像学检查确认毁损部位及毁损范围。多轮多次毁损有提高疗效的潜力,但应警惕出现永久性并发症的风险[42]。
临床问题10:通过哪些手段可以实现GMH全切除?
推荐意见13:采用电生理监测结合神经导航技术可以提高病理灶全切除的概率,可通过术中对痫性放电的监测指导切除范围的界定,若合并其他脑部异常应当考虑扩大切除范围(推荐比例93.5%,反对比例0.0%)。
对于双侧、多发或连续型病灶的PNH,以及SBH等通常与皮层存在广泛功能联系的病灶,或位于重要功能区、脑深部的病灶,传统切除手术的疗效往往较差;范围局限的单侧病灶,尤其是单侧单发结节型灰质异位切除术后效果良好。
为准确定位病灶、明确切除范围,术中应采用电生理监测结合神经导航技术。术前用导航在头皮投影异位病灶位置,可指引设计最佳的手术切口和骨窗范围。开颅后首先在异位病灶及周围皮质表面使用皮层电极描记放电情况,进一步确认癫痫样异常放电范围,包括异位病灶、上覆皮层、或同时来自异位病灶和功能连接的皮层[23,43]。在标记出痫性放电区域后,进一步确定切除范围。异位病灶周围的异常白质的切除也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导航的应用可指引皮层切口位置,通过最短的距离、最合适的脑沟裂进入脑深部,同时最大程度地避免正常皮层损伤。建议在显微镜下实施病变切除术。病变切除后再次描记深部脑电或皮层脑电,观察痫性放电是否消失,并分别用导航、显微镜确认病变是否残留,在痫性放电密集区域继续切除,若病变位于功能区则可避开皮层血管施行低功率皮质热灼。
术中超声对于分辨白质灰质也有很好的效果,且具有实时、便捷的优点,故可应用术中超声辅助术中神经导航对异位病灶进行精确定位,并可评价术后疗效。术中超声要求超声医师操作前仔细观察MRI图像,确定异位病灶的位置及形态,在术中仔细辨别异位病灶与周围正常组织,以配合手术医师完成准确定位、完全切除异位病灶。
GMH可能合并其他脑皮质畸形,必须通过系统全面采集异位病灶、上覆皮质、畸形皮质和可能出现的致痫灶信号,以更准确地描绘致痫网络、定位致痫灶、确定切除范围。若GMH合并海马硬化,且通过深部电极检查发现异位病灶与硬化海马或颞叶内侧存在同步放电,这时除了切除异位病灶还应同时行硬化海马、颞叶前部切除术,以达到更好的癫痫控制效果[44]。
临床问题11:通过哪些手段可以实现MCD全切除?
推荐意见14:不同MCD的解剖位置和与其功能联系的皮质范围有所不同,电生理监测及神经导航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采取扩大切除的方式以完全切除致痫灶(推荐比例93.5%,反对比例0.0%)。
对于其他MCD,也可采用电生理监测结合神经导航技术。与GMH全切除相似,开颅后先用导航确定畸形皮质的位置和范围,再使用皮层电极描记确定致痫灶的位置和范围。在导航指引下切除痫性放电区域后,再将残余的仍有痫性波发放的异常区域切除直至消失。致痫灶位于功能区者,可行小功率皮质热灼术或多软膜下横纤维切断术。每类MCD的全切除方式应充分考虑其解剖范围与功能联系的皮质范围。对于范围窄、体积小的局灶性病变,可优先考虑对局部致痫灶进行完全切除,比如对于结节性硬化,若异常放电起源于致痫结节及临近皮质,则在完全切除致痫结节的同时切除周边一定区域的组织更为有效[28,29];对于HH,完全切除对于体积较小且带蒂团块的疗效尤其明显,而对较大、广泛附着于下丘脑的病变可经额眶颧入路或采取脑室-颅底联合入路以提高全切除概率[45,46];对于脑裂畸形,可将脑裂畸形边缘的皮质、裂隙内的异位灰质进行完全切除[30]。对于广泛性病变,比如弥漫性多小脑回畸形,可尽早采用多脑叶切除术,改良大脑半球切除术或半球离断术;对于双侧无脑回畸形,虽然目前大多采用药物治疗来改善症状,不过也有报道通过全胼胝体切开术缓解了癫痫发作[47]。而对于小头畸形、重型前脑无裂畸形等极其严重、广泛影响皮质的病变,一般不考虑切除性手术治疗。
六 癫痫术后早期癫痫发作的防治
临床问题12:哪些因素可以影响癫痫术后早期癫痫发作的发生?
推荐意见15:癫痫患者术后早期癫痫发作主要与起病年龄、病程、发作类型、术前发作频率、手术切除部位、手术方式等有关。围手术期停用抗癫痫发作药物引起血药浓度下降,手术本身对大脑皮层的刺激,围术期的感染、低血钠、代谢性酸中毒等并发症也可引起术后早期癫痫发作(推荐比例100%,反对比例0.0%)。
术后早期癫痫是癫痫外科常见的现象之一,是指术后住院期间,特别是术后1周内发生的癫痫发作现象。起病年龄小、病程长、多灶起源的患者发生术后早期癫痫的概率较高[48,49]。手术切除部位也是影响术后早发癫痫的重要因素。颞叶癫痫术后早期癫痫的比例低于颞叶外癫痫手术。全面性癫痫、癫痫性脑病等行胼胝体切开术等姑息性手术,术后疗效较差,术后早期癫痫发作也更频繁。围手术期停用抗癫痫药引起血药浓度下降,可引起患者原有癫痫发作加重或者出现新的癫痫发作[50]。手术中脑组织的过分牵拉、挫伤、血管损伤,以及术后的组织瘢痕等是手术致痫的主要诱发因素。围术期的并发症,如感染、低血钠、代谢性酸中毒等降低癫痫发作的阈值,也是术后癫痫发生的重要诱因[51,52]。
临床问题13:如何预防癫痫术后早期癫痫发作?
推荐意见16:为预防术后早期癫痫的发生,需要避免各种可能诱发因素的发生,及时处理各种并发症,如出血、感染、皮下积液等,预防性使用抗癫痫发作药物(推荐比例93.5%,反对比例0.0%)。
为预防术后早期癫痫的发生,需要在手术中尽量减少脑组织的损伤,尽量缩短手术时间。同时在围手术期,需要避免各种诱发因素,规范使用抗癫痫发作药物。
避免诱发因素的发生。尽量减少对患者刺激和各种应激因素;术后给予患者吸氧避免脑缺氧的发生,及时处理脑水肿、发热、颅内感染等并发症;减少和避免使用对抗癫痫药物或对癫痫发作有影响的药物,如喹诺酮类抗生素等。
预防性应用抗癫痫发作药物。为减少术前服用药物的突然中断对患者的影响,术前的药物应当在手术当日继续服用[53],术后尽早恢复使用。也可以根据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发作类型使用相对应的抗癫痫发作药物。围手术期应尽量选用广谱、高效、安全、快速、不影响意识、对生命体征影响小、多种剂型可选的抗癫痫发作药物。尽可能选择相互作用少的药物,特别要注意抗癫痫发作药物的不良反应,必要时监测血药浓度。常用的静脉注射药物为丙戊酸钠注射液[54],应用的主要方法是术后30min内给首次负荷量,然后1h内开始持续静脉滴注,在患者开始口服抗癫发作药物药物12h后停用静脉滴注。口服药物可选:丙戊酸钠、左乙拉西坦、卡马西平和奥卡西平等。
临床问题14:出现癫痫术后早期癫痫发作如何处理?
推荐意见17:癫痫术后早期发作应积极寻找病因,选择合适的抗癫痫发作药物进行治疗,防止继发性脑损伤(推荐比例100%,反对比例0.0%)。
术后早期出现癫痫发作,需要分析相关诱发因素,在及时去除诱发因素的同时调整抗癫痫发作药物,必要时监测血药浓度。对于局灶性的癫痫发作,可以观察病情变化,调整口服药物或加大注射用药物用量;如果出现全面强直阵挛性发作,需要给予吸氧和及时安定静脉注射治疗,防止产生脑损害;如果出现癫痫持续状态,特别是惊厥性持续状态,需要紧急抢救处理,及时终止发作。
审稿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小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毛之奇(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田宏(中日友好医院)、冯卫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任杰(昆明三博脑科医院)、刘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刘婷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刘翔宇(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杨岸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吴洵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张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张春青(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陈心(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季涛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孟强(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徐硕(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徐成伟(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薇(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郭燕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梁树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彭伟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星(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操德智(深圳市儿童医院)
外审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杨卫东(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杨天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张建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姜玉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顾硕(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遇涛(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无利益冲突。
上下滑动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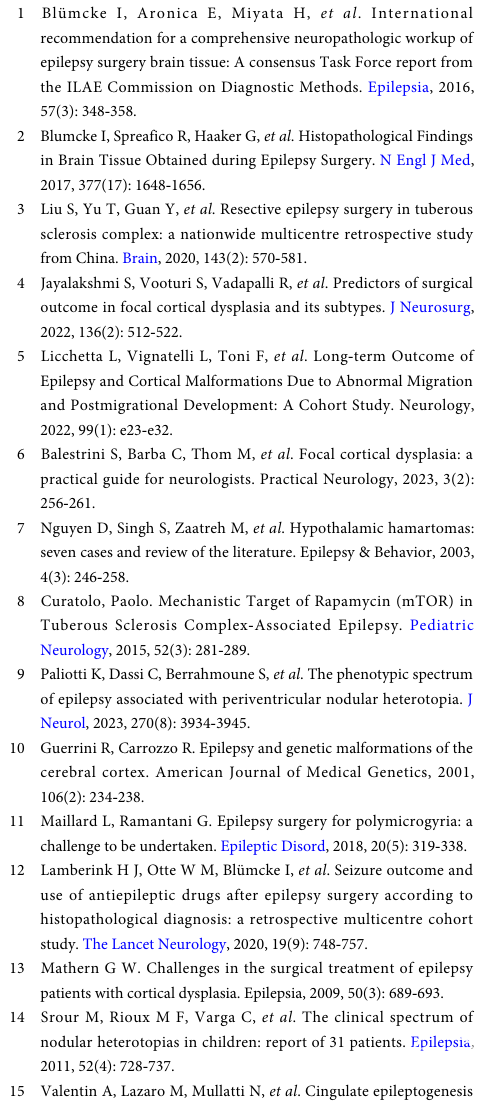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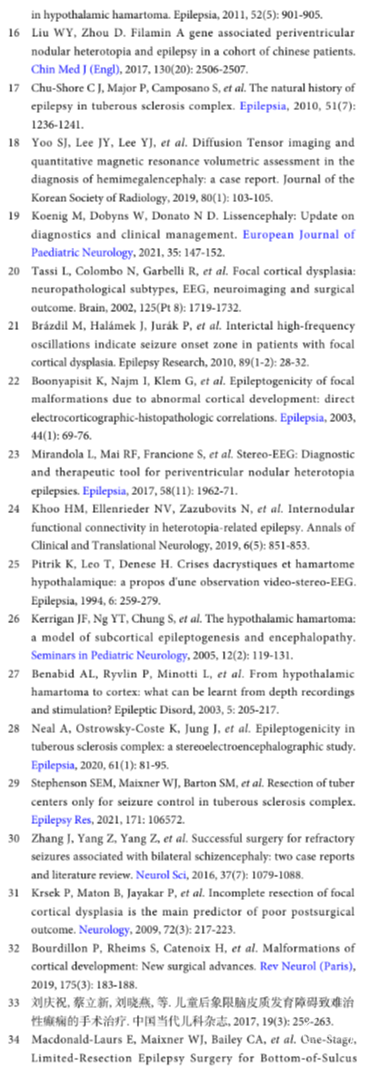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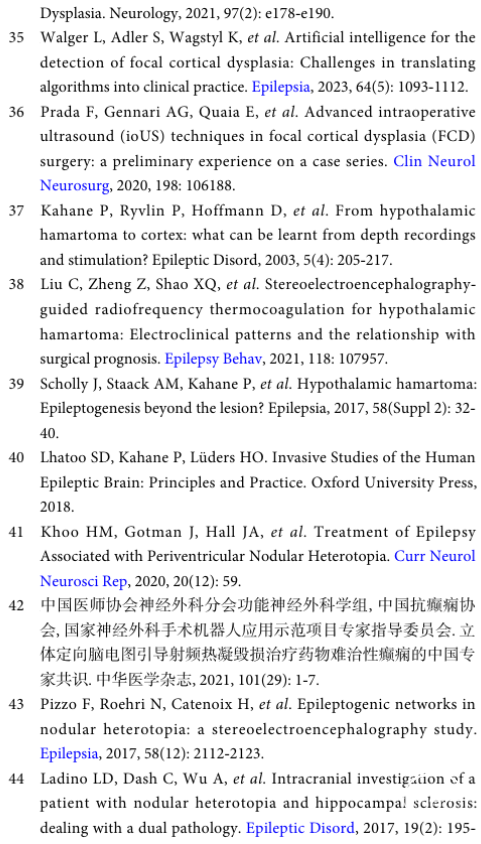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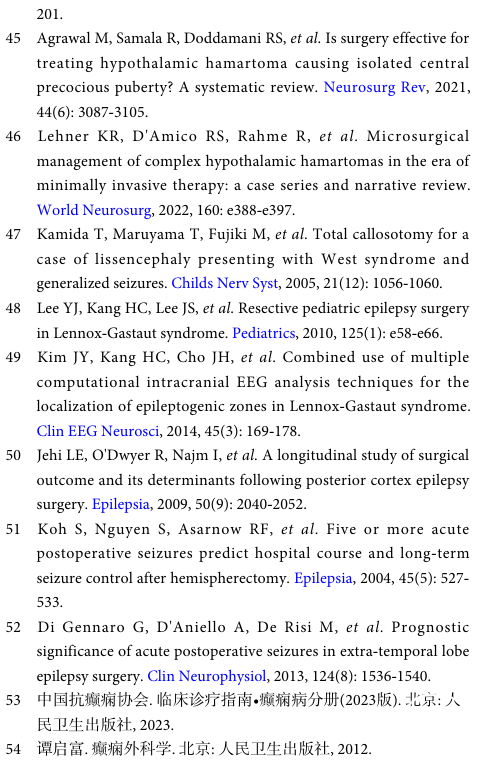
上下滑动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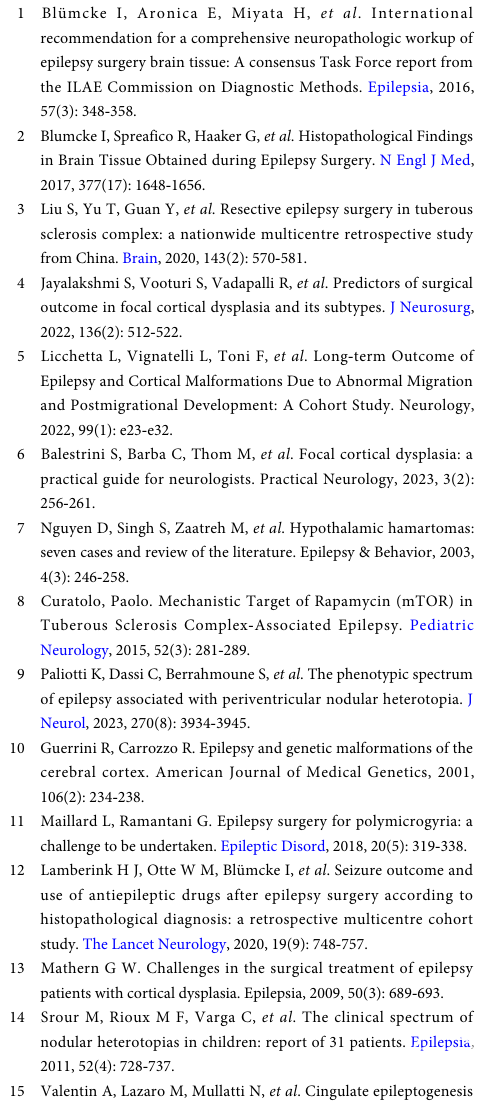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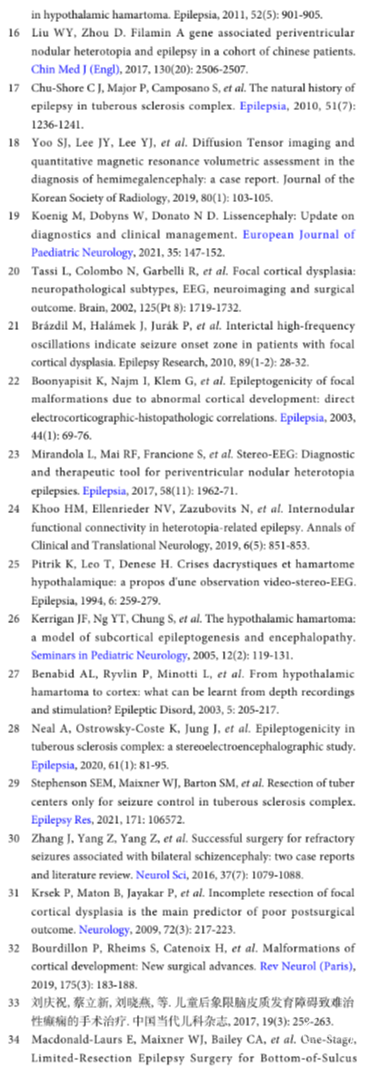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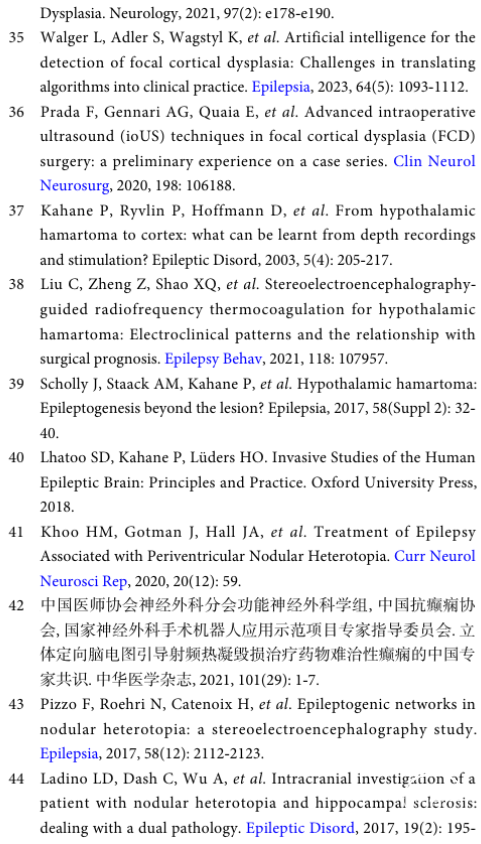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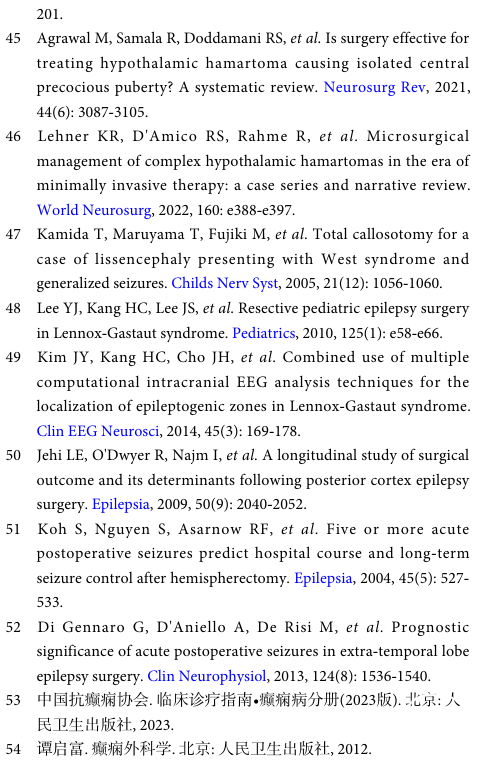
![]()
声明:脑医汇旗下神外资讯、神介资讯、神内资讯、脑医咨询、Ai Brain 所发表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脑医汇及主办方、原作者等相关权利人所有。
投稿邮箱:NAOYIHUI@163.com
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裁切、录制等。经许可授权使用,亦须注明来源。欢迎转发、分享。









